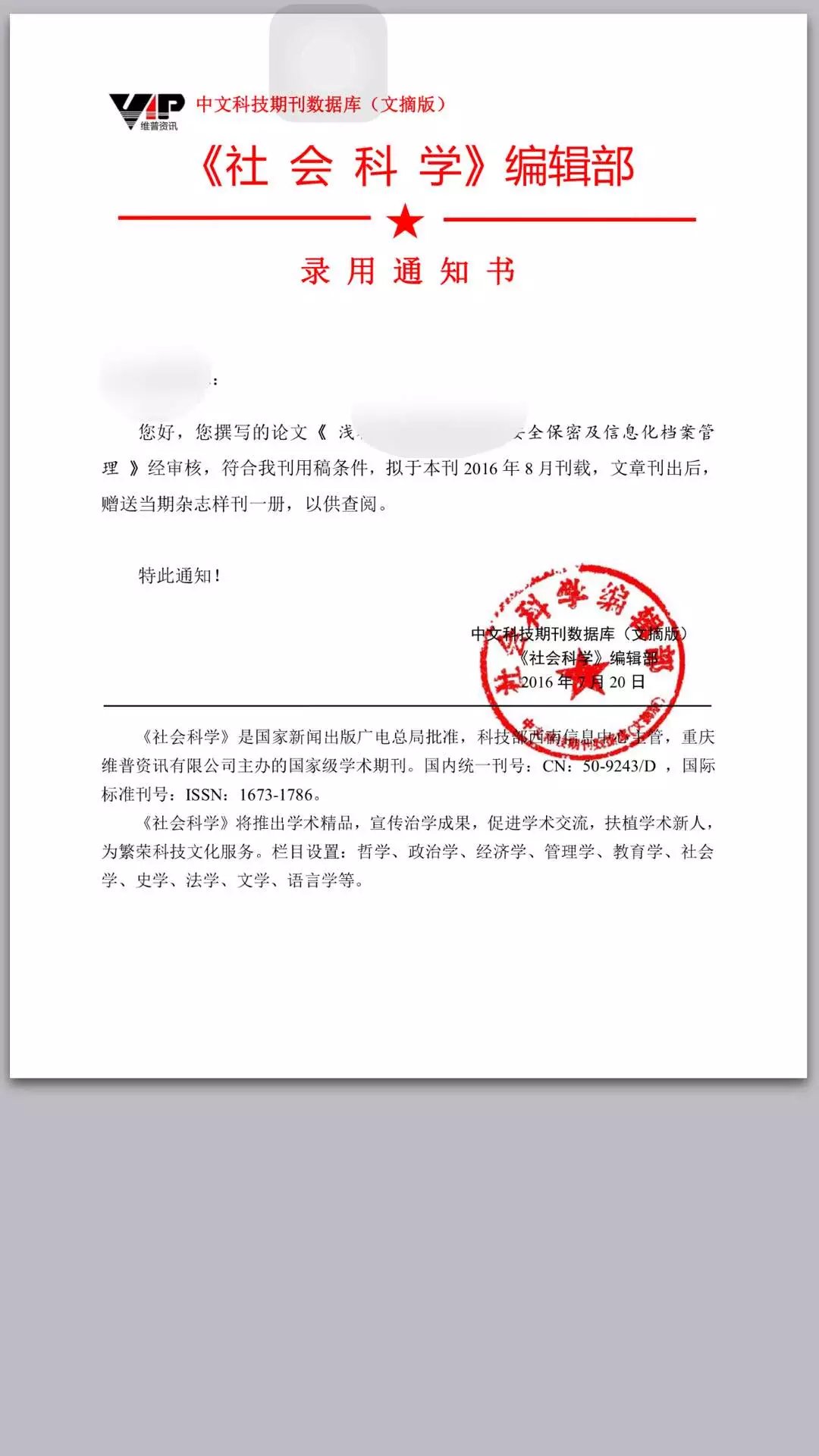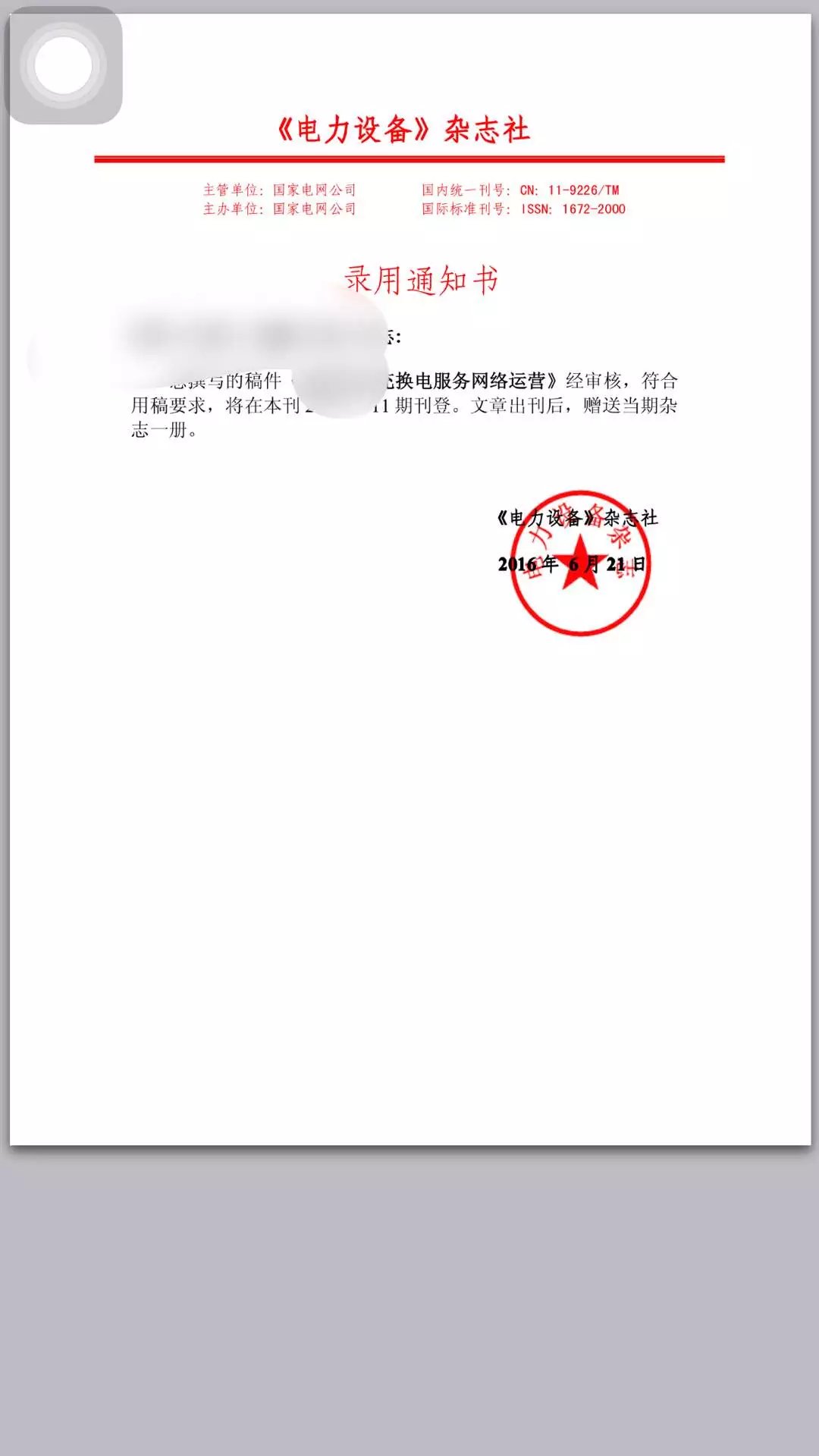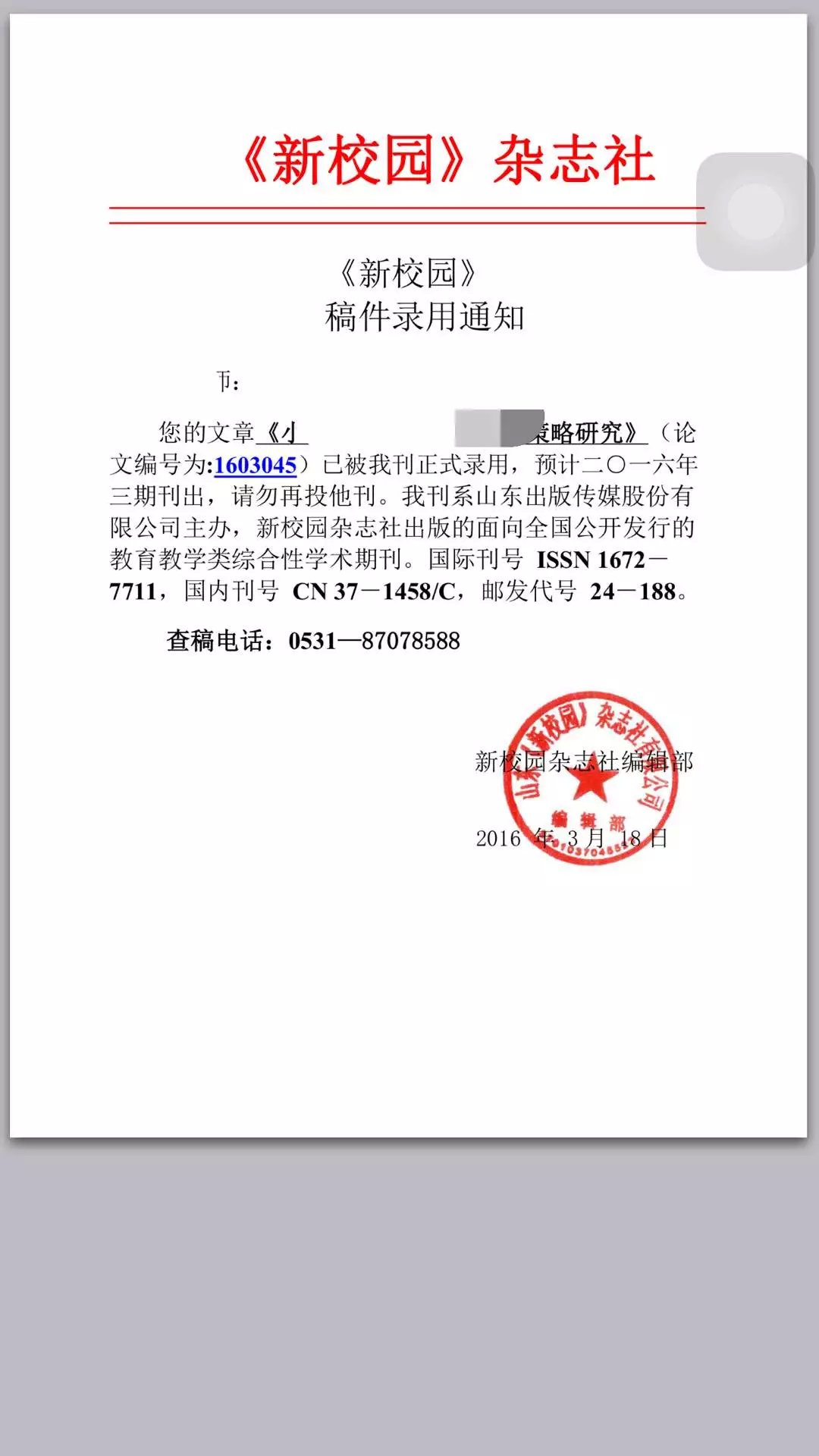伤痕文学与解冻文学的走向
1979年初丁玲复出于文坛时,“伤痕文学”业已蔚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潮,并由此引发了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的激烈论争。受“五四文学传统”和“革命文学传统”这两种不同文学传统的影响,她在这场文学论争中表现出了相当复杂、矛盾的态度。在复出之初,她几乎同时捧出了具有不同思想性质的《“牛棚”小品》与《杜晚香》。前者是在“伤痕文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写就的,它通过对“牛棚”生活中三个片段的回忆,展示了苦难生活中令人感奋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这说明复出后的丁玲在创作精神上仍然坚持和传承了“五四”个性传统和“人的文学”传统。但是,与此同时,她却又以《杜晚香》对此作出了强有力的反拨和矫正。在这篇作品中,丁玲选择了“永远正确”的题材和主题,以歌德型笔调叙写了同名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并将自己对政治功利的追求与道德诉求相聚合。从“左联”时期开始形成、到延安时期确立的“革命文学传统”,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要求作家改造自我、歌颂工农兵“新人”。不难看出,在《杜晚香》中,流淌着的仍然是“革命文学传统”的血液。在这两篇作品发表后,在说到将来的创作时,她明确表示:“我还是应该坚持写《杜晚香》,而不是写《‘牛棚’小品》”。这意味着她写具有社会控诉能量的“伤痕文学”文本,只是偶然的“误入藕花深处”,而《杜晚香》对她而言则具有“方向”的意义。丁玲对这两篇作品的这一褒贬扬抑,间接地表达了她对“伤痕文学”的态度。与此同时及以后,她的这一态度还通过其大量的理论言说得到了直接的表达。
歌颂与暴露
随着“伤痕文学”的兴盛,理论界展开了歌颂与暴露(或曰“歌德”与“缺德”)问题的讨论。1979年1月14日,即丁玲回京两天后,《诗刊》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歌颂与暴露”即是会上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晓风致陈荒煤的信”,以通信方式对写“文革”的“伤痕文学”表示支持。6月,《河北文艺》刊发文艺短论《“歌德”与“缺德”》,认为写“伤痕”就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要求“革命的作家”“为人民大‘歌’其‘德’”。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激烈的争论。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此后一直延续到80年代前期。就在“歌德”与“缺德”问题论争的这一大背景下,复出后的丁玲曾积极为“伤痕文学”申辩,为这股社会关怀思潮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她张扬文学的“真实”性,并从这一角度,阐述了“伤痕文学”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她看到,“十年大乱,国家民族大好河山被糟蹋得乱七八糟,大家从心里、从感情上都有怨恨,我们现在有些人写对‘四人帮’的恨”,这是必然的。她赞同文学创作要“说真话”,“怎么能说假话呢?那成了骗子”。在她看来,“文艺就得真实”,难道“不写真的还写假的?”“写光明难道就能不写黑暗、不鞭打黑暗了吗?”1980年7月,在上海接受《文汇增刊》记者采访时,她重申:“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都不说真话,都不能说坏,只能说好,讳疾忌医,这怎么行呢?……我们这个社会的弊病,可以写,应该进行自我批评。”
其次,她积极鼓吹文学的战斗性,并从这一角度,高度评价了“伤痕文学”干预现实的战斗精神和现实价值。她认为,文学应成为战斗武器,应该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揭露不良倾向,如果“不揭露不好的,尽歌功颂德,尽包庇坏人,那还算什么文学呢?”从这一价值观出发,她肯定“伤痕”小说“是在文艺上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直到1983年2月,她在回顾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时,对重在“暴露”的“伤痕文学”仍然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几年文学创作发展的进程是历史的必然,是一定要有的,即使其中有的骂了很多人,骂了大街,也自有它的道理,因为有该骂的人嘛,骂得我们心里痛快!”
再次,她在宏观上为“伤痕文学”的合法性作出辩护后,还在微观层面上对许多“伤痕文学”作品作出了肯定性评论。1980年6月,她为黄蓓佳的短篇小说集《小船,小船》作序,称赞其中的《阿兔》“令人深思”:它“反映了‘四人帮’横行时代给予我们年轻一代的创伤”。同年12月4日,读完《一个冬天的童话》,认为“较有深度”。1981年春,她评价《人到中年》和《李顺大造屋》说,前者“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普遍存在着的社会问题”;后者“刻划的农民形象,反映的农村生活,都是真实生动的”。1981年11月23日,她在加拿大就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发表演讲,特别提及《班主任》、《伤痕》等“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赞赏这些作品的作者“感时忧世,敢想敢说”,“是最有希望的一代”。
根据丁玲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伤痕文学”合法性所作的申辩,在“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中,是很可以把她归入“暴露”派行列的。但是,丁玲的复杂性就在于:一方面,她为“伤痕文学”申辩,但另一方面,她又高举起“歌德”旗帜,对“伤痕文学”作了自觉不自觉的否定。她认为,作家们“可以献上一些颂辞,有德可歌,还是可以歌的”;并要求作家站稳立场,“为党颂德,为人民说话”。在她看来,“写黑暗”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只是为了衬托光明(所谓“光明是靠黑暗显示出来的”);并宣称:“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会说我是一个歌德派。是的,我是赞成歌人民之德的!歌社会主义之德的。” 她不但以《杜晚香》表现出了“歌德”倾向,而且于1981年6月建党60周年前夕写出了“歌德”的长诗,题目即为《歌德之歌》。有人向她建议把题目改为“献给党之歌”,但她却断然说:“不,还是‘歌德’好,别人是别人,不管他”,并表示哪怕群众不理解也要这样写。联系文坛上“歌德”与“缺德”争论的背景,她对这首长诗的命名该不是无意的吧。
丁玲强调要做“歌德派”,要歌党之德、歌人民之德、歌社会主义之德,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丁玲常常把“歌德”当成了唯一的价值取向,并把它与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对立起来,似乎一写“问题”,就违背了“歌德”之旨。她认为:
……国家的问题太多,总是要有人来挑担子,作家也应该分担自己的一份。一个作家,如果不关心这个困难,不理解挑担子的人的难处,你老是写问题,那么,你的作品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一定要写得我们国家那么毫无希望,才算思想解放吗?……你不帮忙,你在那里老是挑剔,那有什么好处?
总之,她既承认国家问题很多,又反对“老是写问题”。在她看来,如果“老是写问题”,在态度上就不是“帮忙”而是“挑剔”,在性质上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显得“毫无希望”,在结果上对国家民族就没有好处。这就给人以有问题而不能写问题之感。当然,她也看到,在偌大一个国家里,总会出现一些不合理想的事,产生“各色各样的悲剧”。但她认为,“这类事最好不写”;如果要写,也“不要写得哭哭啼啼,悲悲切切,灰心丧气,……而要把处在苦难中的人物写得坚定、豪迈、泰然,把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亲密、庄重、神圣、无私,这就更显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是如何可爱”。根据丁玲所倡导的这种写法,对社会主义时期“各色各样的悲剧”的描写,实际上却成了对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歌颂。这样,“问题”本身往往也就被掩盖而不成其为问题了。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丁玲对“伤痕文学”思潮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伤痕文学”,顾名思义,本是以“暴露”(暴露“文革”和极左路线的错误及恶果)为目的的文学,是勇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积极干预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但丁玲却更以一种理想主义的规范去要求它、制约它,因而,在她的相关言论中始终贯穿了“虽然――但是”、“不仅――更要”式的转折或递进式的置重于后者的思路。这一思路就是她在1980年7月所作的《谈谈文艺创作》中所概括的“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对这一观点,她作了反复的阐释、引申。1980年10月,在给孙犁的信中,她写道:“我认为写现在,写动乱,写伤痕,写特权,写腐化,写黑暗,可是也要写新生的,写希望,写光明。” 1983年11月,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中,丁玲批评“伤痕文学”作家“错把‘四人帮’当成整个的党,把‘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十年看成是整个革命历史,因此他们当中,有的人对党、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表示冷淡,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并将之列入“有关文艺创作的错误思想和言行”之首,有把它视为文艺界“精神污染”表现之嫌。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丁玲所表述的文学创作中有关社会生活的内容范畴和主题倾向是全面的,也是可取的,因为相关的文学创作的内容范畴和主题倾向,取其大者,大约就是“暴露”(即“写黑暗”、“写缺点”)与“歌颂”(即“写光明”、“写希望”)这两个方面。但是,如果把它置放于特定的文学语境中,则丁玲显然有以“全面”来否定“伤痕文学”这一特定的“片面”(局部)之嫌。因为对于具体一篇“伤痕文学”作品而言,要使之在“暴露”的同时还有“歌颂”,这显然是一种打压式的苛求。她在具体论述中所贯穿的这种转折或递进式的思路,更在目的上把“歌颂”置于“暴露”之上,这就极易造成对“伤痕文学”合法性的否定。她批评某些“伤痕文学”作品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即“由针砭发展为诅咒,由对于某些个人的指责而发展到对整个社会的控诉”),正是这一思路导致的必然结果。
丁玲对伤痕文学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导致了她对其中一些作品作出了过苛的指责。她批评《春天的童话》“尽管它揭露了何净这样的人物,但它的总倾向我不赞成。如果我们的作家都是这样的心灵,那我们的创作就危险了”。在她看来,似乎如果单是“揭露”而没有“赞美”,那么,作家的心灵就“不美”了,“格调和境界”就不高了,创作就危险了。1981年,丁玲对符合其“不仅――更要”式理想模式的张贤亮的《灵与肉》及据此改编的电影《牧马人》作过较高的评价,但三年后在中宣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她对作者的另一篇小说《绿化树》却作出了相当严苛的批评。这篇作品重点是写主人公章永�在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启示和劳动人民善良品德的浸染下人性复苏的过程,是以“写光明”为主的作品。但由于作者是把这一过程的描写置放于主人公被打成右派后在三年困难时期遭受磨难的背景之中,所以在一定程度也继承了“伤痕文学”的遗绪。尽管如此,丁玲却明确表示:“我不喜欢这篇小说,我觉得太过分了”。她置任何历史具体性于不顾,而指责主人公在“饥饿、贫困”之中“像个狼孩”,“他们之间只有饿狗争食那种关系”,并进而指责作品“使人感到是共产党把人变成了兽这个世界太阴暗”。这就连“不仅”也不能有了,剩下来的就只有“更有”――即“歌德”了。
“本我”与“自我”
由上可见,丁玲在有关“伤痕文学”的论争中,表现出了鲜明的二元态度。不管是她相关的文学创作还是理论言说,都具有两极性。如果择其一端,我们大可以把她派入“伤痕文学”的支持者或反对者行列(或政治上、思想上的“左”与“右”的行列)。这种二元态度正是晚年丁玲思想矛盾的真实呈现。但根据她对《杜晚香》“方向性”意义的强调和在理论言说中对那种转折或递进思路的使用,从总体上来看,当时传出来的“丁玲不支持伤痕文学的说法”,并非无稽之谈。
丁玲对“伤痕文学”两极性态度的形成,是“两种文学传统”影响的结果。但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去汲取这两种不同的文学资源,却有赖丁玲本人的抉择――这自然是以她对自己当下处境的体认以及现实需要为基础的。作为20多年前就被打倒的右派,丁玲较之“文革”中遭难的人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有着更为刻骨铭心的惨痛体验。1979年11月,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她比较了二者的不同:“我们同样遭难,却不一样”――后者“虽说被打倒了,可是是香的,因为你不投‘四人帮’嘛”;但前者“是臭的!是被我们自己人划的,二十多年批倒批臭!”在其个人化的文本中,丁玲更是袒露出了在左的错误迫害下产生的那种“怆然”、愤然心态:“静坐院中,看树影东移,夜凉如水,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以她的这一经历和这种深入骨髓的惨痛体验,她“大可以从事足以表现受难的时代的宏伟叙事”,去揭露“伤痕”背后的社会成因(她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被打倒,不是由于哪一个人,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从忠实于“本我”的真实要求出发,为了履行生命的第一原则――快乐原则、消除使自己感到痛苦的紧张体验,她确也曾经产生过这样的表现和控诉的冲动。继承“五四文学传统”的《“牛棚”小品》以及她为“伤痕文学”申辩的言论,就是其在文学创作和理论言说层面将这一表现和控诉的冲动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外化的结果。
但是,这一“本我”的冲动在更多的情况下,却被她的“自我”抑制了。这清楚地表现在一篇短文从构思到流产的过程中。1978年10月8日,亦即在小说《伤痕》发表不到两个月之时,她“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师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从她在这则日记中对情节和主题的概要记述来看,这篇孕育中的作品,在性质上应属“表现受难的时代的宏伟叙事”,是《伤痕》式的揭露现实伤痕、最具社会批判能量的控诉型文本。但是,她“一觉醒来,又有所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从丁玲的这段自我表述来看,其控制“本我”的“自我”,应该是被“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曾经给她制造过“旧的伤痕”的政治伦理原则所抑制了的。为了避免不愉快和遭受痛苦(“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它依据现实原则去调节、压制本能活动,以现实原则代替了“本我”的快乐原则。从这篇作品最初孕育到最后胎死腹中的短暂历程,我们可以管窥到丁玲“本我”的原始的宣泄冲动以及它如何被“自我”抑制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她最终放弃“表现受难的时代的宏伟叙事”,固然是“自动”的(出于“自我”的现实原则),但对“本我”而言,却远不是“自愿”的。
丁玲的“本我”被“自我”所抑制,还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她对《苦恋》的充满矛盾的评价中。白桦等人的电影剧本《苦恋》是“伤痕文学”中一个较有深度的暴露型文本。“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持续了两年的争论,并在文坛上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而成了整个“伤痕文学”争论中的一个焦点。《苦恋》展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并对社会体制的弊端提出了追问。在主题范畴和情感倾向上,它与上述丁玲孕育中的小说是完全相通的。但是,依据“自我”的现实原则,在批评《苦恋》的高潮中,丁玲多次撰文或发表讲话,对《苦恋》作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她通过与《牧马人》的比较,对《苦恋》的主题倾向作出了否定,认为“同样是苦恋,但一个健康,一个不健康;一个起积极作用,一个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其之所以“不健康”,是因为作者“在动笔的时候,为了表现‘苦’,就失去了分寸,把平日深埋在心底的一点小小委屈的火花闪亮了,信笔所至,淋漓尽至,编造了一些不现实的生活、情节,流露出一种并不健康的情绪,使读者和观众感到诧异,感到委屈,感到愤慨”。缘此,她指称《苦恋》“有错误倾向”。直到1984年,在批评《苦恋》的高潮早已过去后,她还将《苦恋》翻检出来,通过与《洗礼》的隐晦比较,仍然指陈它是一个“不好的作品”:《洗礼》“里面写到‘四人帮’时期,残酷黑暗的东西不比《苦恋》少”,“于是,我就想到,有些不好的作品,不一定非批评不可,如果有好作品(譬如《洗礼》)拿出来,就把那个不好的作品比下去了,批判了”。
丁玲对《苦恋》的严厉批评,是奉行“自我”的现实原则的结果。而她的“本我”则是趋向于对之认同的,这可以从她个人化的文本中窥见端倪。1981年6月4日,即在《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后约一个半月后,在她向友人倾吐内心的信中,这一“本我”得到了真实的呈现:“不管现在左的也好,右的也好,究竟对我们如何看法,如何对待,是大可寻思的。我明确的告诉你,假如《苦恋》是我写的,你可以想见那些左的右的都会汇成一股洪流来围剿的。难道二十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不学一点乖吗?文艺事大不可为,希望在五十年后”。在这里,她作出了一个饶有深意的设定――“假如《苦恋》是我写的”。这看上去是一个假设,但与她日记里记述的那篇小说的构思比较,何尝不是她“本我”的真实流露?进而言之,如果她没有这样真实的内心要求,她何以作出这样的设定?但是,她的这一“本我”刚刚露出冰山一角,便很快被“自我”的现实原则淹没了――即“那些左的右的都会汇成一股洪流来围剿”。在这里,丁玲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如果《苦恋》是她所写,其事态的严重性会变得较白桦更甚。这既关乎丁玲对自我处境的体认,也关乎她借回避(乃至躲避)以远祸之心态的形成原因。白桦的《苦恋》问世以后,受到了某些方面人士的严肃批评(乃至批判)。这些批评者在思想倾向上事实上只能是丁玲所指称的“左的右的”中的一种。而丁玲在这个假设中所假定的“围剿”者却是二者的合流。这是因为在丁玲自己看来,她既是曾经被打入另册的人、又是在现实中仍然引起争议的人,所以,她的自我处境较之白桦更加不堪。虽然此时组织生活在历经曲折后终于得到恢复,但历史问题尚未澄清,她的平反还留有尾巴。这成了她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一块掀不掉的石头。“这压在心上的沉重石块,不能不影响到她晚年的心境和处事”。1984年夏中组部为她恢复名誉后,她在谈及前几年的心情时曾说过:“谁看到我都认为我精神很好,认为我心情很好……可是,有谁知道在我心底里还压着这样一块沉重的石头?我能向谁诉说呢?我只能这样活下去,别无选择。”因此,为了有助于自己历史问题的最后解决,为了推翻那块压在心上的沉重的石头,她几乎是“别无选择”地选择了“谨慎”、“学乖”,而绝对不能再授人以柄。她的疲惫的心灵再也经不住新的打击,她所需要的是“平静”。对此,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得分明:“我是一个适合于住在乡村的人了,一切关系简单。我的年龄也不准许我负担任何工作和问题。身体可以劳累,心灵再也受不住打击了。躲在鼓浪屿,世外桃源,还是能心情平静的。”从这种心理出发,为了避免不谙政治而遭受新的心灵打击,她不得不关注政治,不得不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不得不去斟酌、去“寻思”“左的也好,右的也好,究竟对我们如何看法,如何对待”。从这一意义上说,丁玲对政治伦理的敏感又是一种被动的选择。这瞻前顾后的“寻思”,其结果自然只能导致她的“畏惧”和对“伤痕文学”相当程度上的放弃。
总之,“丁玲不支持伤痕文学”,是她奉行“自我”的现实原则、压抑“本我”的快乐原则的结果。为了避免遭受新的痛苦,在现实层面上,她惟有抑制和雪藏内心的“怆然”和愤然,“惟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而一旦她将“挣扎”的目的定位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我们也就大体上可以明白她“挣扎”的方向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伦理层面上,她根据自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忖度,一再宣称:“个人心灵上、身体上的伤痕,和国家的、人民的创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肉体的伤,心灵的伤,你的伤,我的伤,哪里能比得过党的伤?”并以“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豁达姿态,表示自己“绝不能沉湎于昨天的痛苦而呻吟叹息,也不能为抒发过去的忧怨而对现今多所挑剔”。这一态度,自然导致了其在文学场域对“革命文学传统”资源的更多汲取,导致了她对“伤痕文学”过苛的挑剔。
更多网站公告
- ·国家级杂志《社会科学》刊期说明 2016-07-20
- · 国家电网主管主办的电力专业期 2016-06-23
- · 办公类核心期刊《办公室业务》刊 2016-04-28
- ·《临床肺科杂志》统计源核心期刊 2016-01-22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 2015-01-09
- ·中国教师论文发表网为您出书 2013-02-26
- ·教师发表论文请找中国教师论文发 2010-01-12
- ·中国教师论文发表网郑重承诺 2008-12-28
热门阅读
- ·文学欣赏与文学创作的相互影响 [04月05日]
- ·文学欣赏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影响 [04月05日]
- ·我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评价分 [05月27日]
- ·伤痕文学与解冻文学的走向 [05月27日]
- ·文学教育的功能与特点看文学课教 [05月27日]
- ·结合文学艺术现象理解文学的文学 [05月27日]
- ·探究中职院校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相 [01月26日]
- ·浅析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01月26日]
- ·浅议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 [01月26日]
- ·网络环境下的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 [01月26日]

电话:15554080077 邮箱:chinajiaoshi@163.com QQ:546427774 102763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