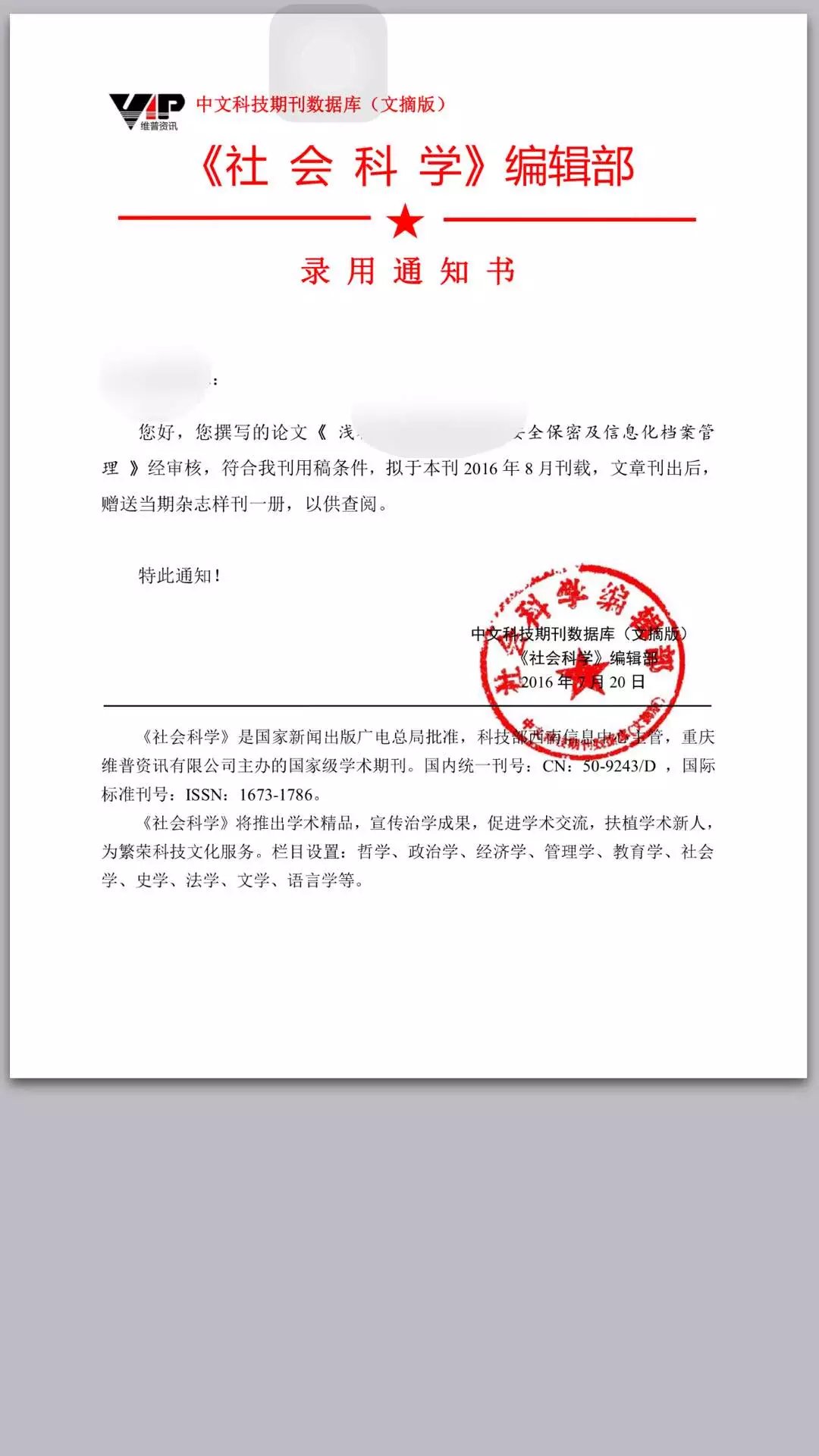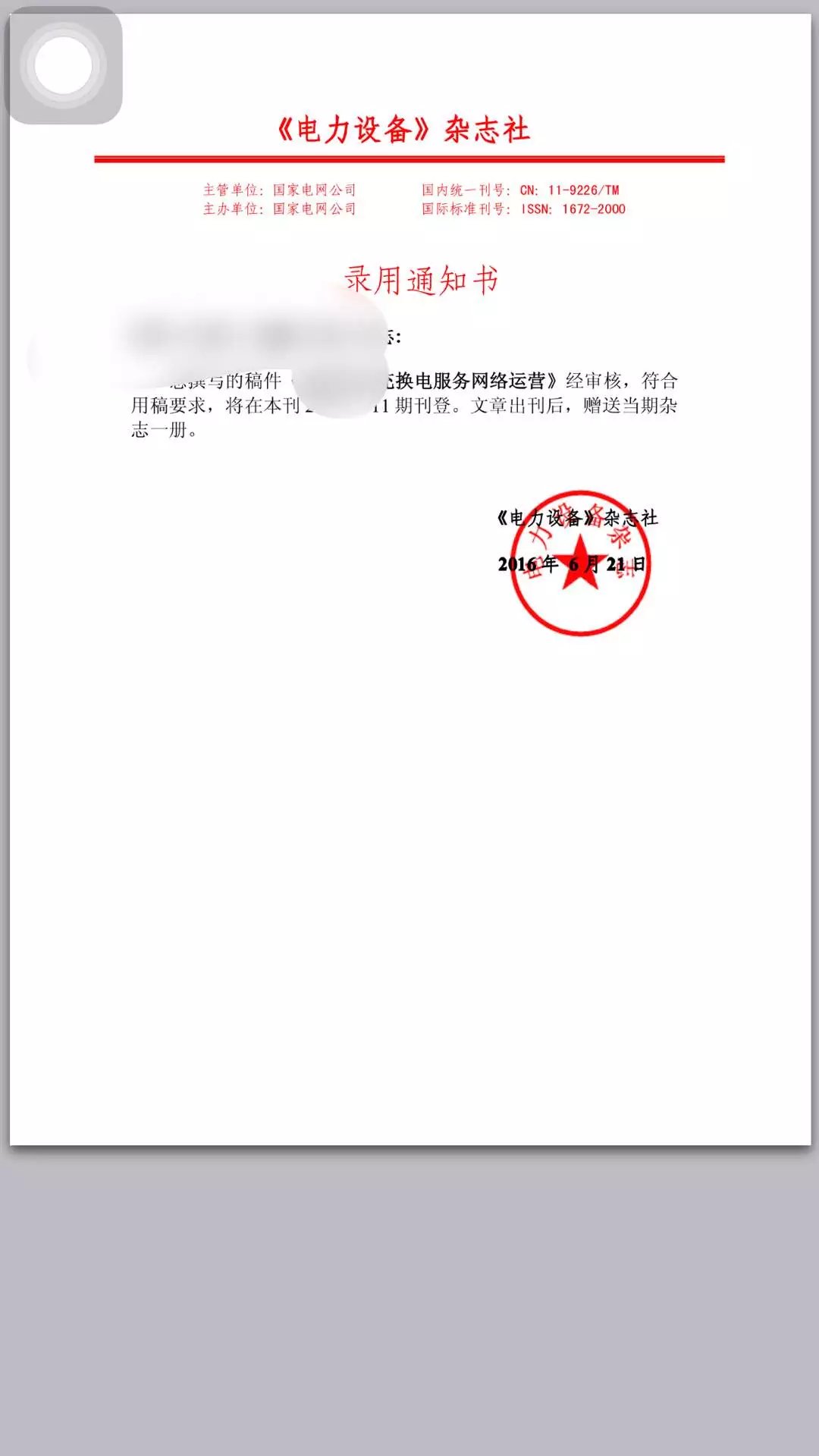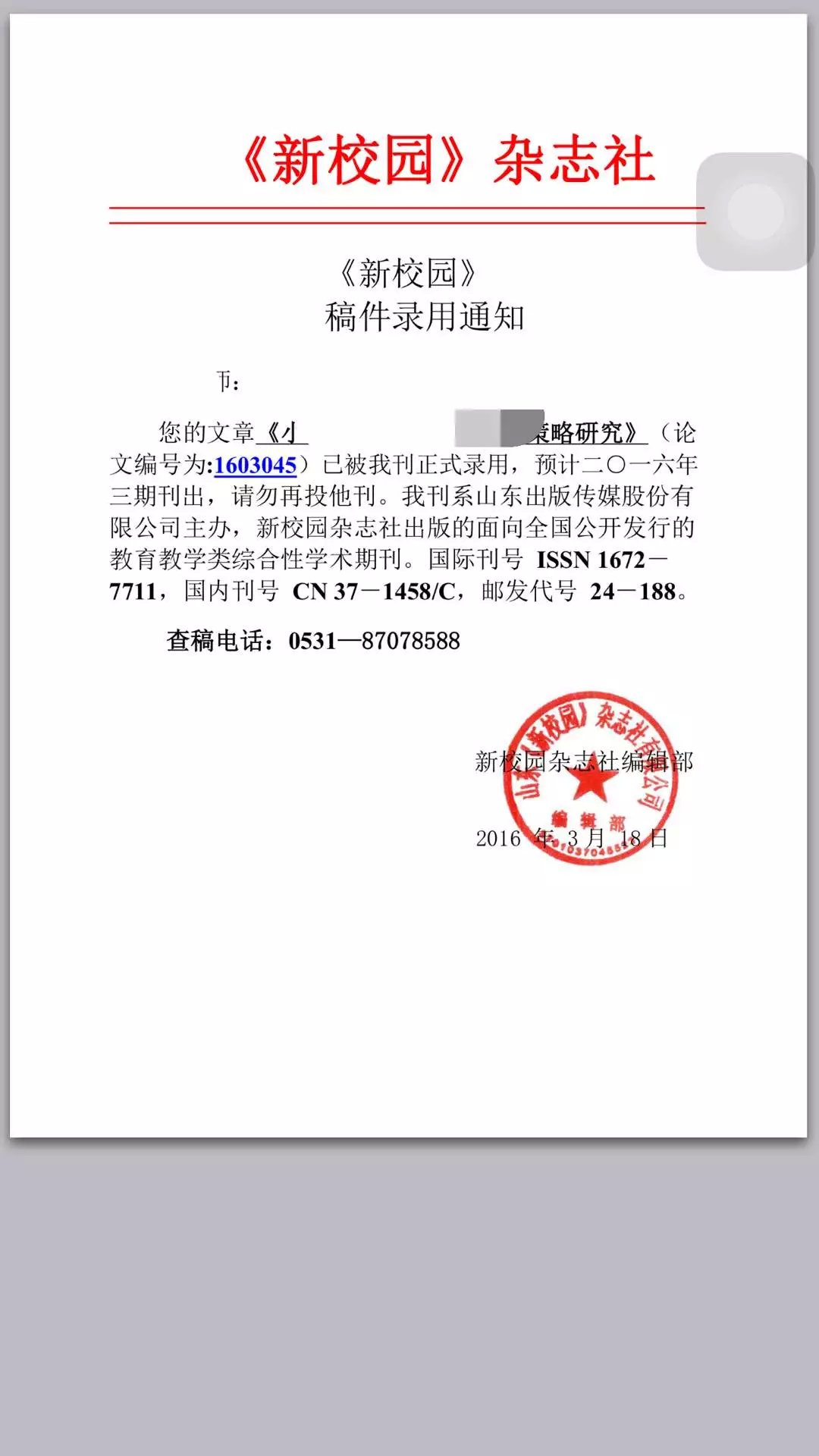当代教育哲学的“问题哲学”转向
摘要:知识论倾向、演绎式思维以及问题意识的缺乏,既是当下教育哲学危机之表现,也是其产生之原因。而教育哲学之拯救,迫切需要教育哲学深刻的范式转换。直面问题是中国教育哲学当下最高意义的范式转换。“问题”对于教育哲学的优先性关涉教育哲学的本性。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既意味着某种实践论的取向、文化哲学与社会哲学的取向,也意味着生活世界的取向。
关键词:教育;教育哲学;问题哲学
任何一个教育哲学研究工作者都无法对当前中国教育哲学的“不在状态”置若罔闻。当下的教育哲学仍未走出本质主义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它既无力改造现实,也弱于对日趋复杂的教育问题反思与批判。教育哲学如果仍然期许有所价值就必须直面思想内部以及社会转型的挑战,而这意味着教育哲学需要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型以自我救赎。
一、教育哲学的危机
或许没有哪一个词像“危机”一样更能引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无限遐想了。然而,吊诡的是,一方面是对“危机”的过度诠释,一方面是对“危机”的虚与委蛇,危机的知性论证并未真正触及内在的焦虑,而焦虑本身也并非理性的真诚。“危机”可以是问题,也可以是问题的产物,直面当下教育哲学的危机,也就是对当下教育哲学的精神状况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教育哲学作为一种“研究”,既是对其研究对象的理论自觉,也是对其研究对象言说方式的运用。所谓教育哲学的危机,由此也就表现为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选择与言说方式的取用这两方
面的危机,说到底,是教育哲学“思维方式”的危机。
首先,教育哲学的危机表现为求真思维的知识论化的危机。知识论是中国教育哲学转型最为厚重的历史碱壳。教育哲学向来以求教育之“真理”为己任,并以此作为教育实践的价值规约。这种知识论的求“真”意识并非没有意义,而且也正是这种求真意识成就了教育哲学的学科特性和自我认同。但问题恰恰出在教育哲学对“真理”的想人非非上。当教育哲学宣称其终极使命在于寻获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一劳永逸的解释框架时,教育哲学就有可能变成一种纯粹的修辞学的暴力。知识论化的教育哲学有三个难解的矛盾:一是教育的普遍真理作为一种理念上的“预设”,其来源究竟是逻辑的构造还是生活?如果其来源是逻辑的自我演化,如同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它将失去对生活问题解释的效力;如果其来源是生活,那么一个未经生活检验的先验构造又如何可能?当教育哲学消灭了对普遍真理的怀疑,其立场也就弱于怀疑;二是就真理而言,如果教育哲学已经宣称它找到了所谓教育的真理,那么对真理的占有恰恰意味着对真理的终结,从而也就消解了教育哲学;三是即便我们以不可思议的机遇找到了教育的普遍真理,我们又何以能够知道我们寻获的这一真理不多不少正好是教育的普遍真理?知识论是渴望逻辑化并乞灵于逻辑的,然仅就逻辑而言,鉴于我们的认识能力,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知识论也具有难以解脱的悖论性质。
受近代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一直致力于普遍必然性的确立。但这种对教育本质绝对优先性的确信却对其逻辑上的内在纠结以及历史文化实践的强大挑战完全无能为力。一方面,以绝对同一性为核心的理性体系为了回避论证的无限循环而不得不最终乞灵于信仰从而走向它的反面;另一方面,传统理性主义似乎也无法有效地解释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伦理价值、宗教信仰以及政治文化观念、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形。总体性的压迫没有阻挡住差异的蔓延,理性的承诺也不断暴露出其无力和虚假。对本质之光的智性真诚并没有发现阴影的扑朔迷离,表面平静的原理式寻求下面则隐藏着教育实践非逻辑的滚滚暗流。纠缠于概念的教育哲学无视教育事实,虽然它用一个幻觉的本质建构了一个霸权式的基础主义,但对细节和差异的忽视却使其走向了能指的飘浮。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在罗蒂那里就表现为对作为自然之镜的人心的消解和摧毁,他在其代表作《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明确提出:“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这也是整个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所致力的教育哲学回归事物本身的范式转换。教育哲学关注教育应该是什么的真理性知识虽然具有其合法性及合理性基础,但如果这些真理性知识拒绝了对教育究竟是什么的现实观照,而将教育真理等同于概念或逻辑的游戏,那么我们越是谈及教育,那么我们离教育自身就越远。真理可以是真相,但没有真相也就无所谓真理。古希腊哲学相信生活问题可以通过知识问题来解决,因此试图通过理性从各种意见中分辨出无可置疑的真理来。然而事实上真正可靠的真理只不过是理性对自身的逻辑表达,而不是对事实的表达。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不存在一个能够超越意见世界的真理世界。这是怀疑论从美诺到休谟再到维特根斯坦的有力论证。
其次,教育哲学的危机还表现在教育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上。教育哲学从固步自封到不断地从域外汲取各种思想资源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这无疑基于教育哲学的理论自觉。但由于拒绝了本土经验,教育哲学的研究便出现了怀特海所谓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the fallacy 0f misplacedconcreteness)。当下教育哲学在清理传统教育哲学的知识论范式方面确有成效。但是,当下教育哲学的知识生产不外是将域外研究成果“复制”到教育研究中来,它只是披上了“教育”的外衣而已。教育研究将哲学的研究成果视为某种不证而明的东西,教育哲学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广、验证充其量不外是证明了某种哲学成果在教育领域的适用性。如同人们已经认识到的那样,这种演绎并不提供新知识。然而当下教育哲学研究的问题不是它没有提供新知
识(设若如此,教育哲学只是一种无害的劳而无功),而是当它将哲学的研究成果复制到教育研究中的时候,它提供了一些坏的新知识(当然这些知识并不新,只是对教育哲学来说貌似新颖而已)。原因至为简单而又隐藏至深。因为这些所谓“研究”完全无视教育的特殊性。当教育哲学研究不加区别地将这些思想框架“移植”(而不是经过创造性的解释)到教育领域中的时候,这些思想就难免水土不服。
追求教育哲学的“哲学味儿”是种危险的心态,那种刻意的哲学只有表达的快感而没有真诚的关切。如果教育哲学研究追求的只是逻辑的缜密或语辞的煽情,当下教育哲学所热衷的宏大叙事就只不过是包装精美的空洞无物而已。把重组偏见当成
思考正是当下教育哲学研究必须谨防的精神病变。
最后,当然也许是最重要的,教育哲学危机是教育哲学研究“问题意识”的危机。问题是事物之间的矛盾。问题意识是对问题的觉知。当下教育哲学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根源于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的教育哲学研究是个问题。没有“问题意识”的教育哲学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它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即它不是针对问题的研究。教育的问题有两类,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教育哲学研究设若尚有价值,那么它所研究的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至少应该是个“真问题”。只有真问题才有成为“课题”的价值。所谓“真”,就是在逻辑上为“真”或者在实践上为“真”。如果教育哲学研究不首先判断它所研究的问题究竟是不是一个“真问题”,那么前提的错误就会带来一系列错误。目前教育有很多问题,然而要发现一个“真问题”却并非易事,而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否发现一个“真问题”,这正是当下教育哲学研究的吃紧之处。二是它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即它不知道它研究的是怎样的一个问题,它通过对问题的研究试图解决一个怎样的问题。当然研究者可以通过“美诺悖论”为其研究的无目的性进行逻辑上的辩护,但显然逻辑上的两难不足以成为教育实践的指导或者根据。三是它没有明确的立场。目前教育哲学研究的流行病是有漂亮的文字而没有好的思想。这种书写方式即使读者如坠云雾之中,也反映了作者对他所研究问题的模棱两可。思想的立场是可以商榷的,不过总还是需要的,以此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折衷的思想立场也是立场,但不能把折衷理解为互为相左的观点之间的游移不定。
知识论倾向、演绎式思维以及问题意识的缺乏,既是当下教育哲学危机之表现,也是教育危机产生之原因。而教育哲学之拯救,迫切需要教育哲学深刻的范式转换。当下教育哲学在解释现实时,失去了反思能力;论证现实时,则失去了批判能力。教育哲学只有通过范式转换才可能获得其明确的身份意识,而走向“问题”,则是一个可能的方案。
二、教育哲学:问题的优先性
当我们将研究的视野由单纯的逻辑思辨走向日常生活世界,由教育哲学完备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的建构走向不完备的粗糙现实,由形而上学的应然允诺走向实践的实然观照,由空洞的理想主义规划下降到当下的民生体验,由抽象的人性假设具体到个体的感性经验,中国教育哲学便不得不面对一个生死存亡的范式转换。如同当下哲学研究将研究范式的转换视为自觉,教育哲学目前面临的最为急迫的问题是如何从教育价值的超验论证走向历史实在。超验论证并非没有价值,但是超验论证的宏大叙事正逐渐使我们丧失对生活的敏感;为中国当下的价值情势开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灵丹妙药(“莫里逊氏丸”)也并非毫无价值,但这种抽象的致思方式剥夺了生活的具体与多样性
的统一。真正可怕的其实不是谎言,而是对那些可见事实有意无意的忽略。直面事实是中国教育哲学当下最高意义的范式转换。
哲学须有问题意识。“哲学源于震惊”,是对“问题”的惊奇,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也是围绕“问题”而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问题也就没有哲学。现代西方的解释学对问题的方法论意义作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海德格尔认为,追问是思的虔诚,追问起源于思,而思则是对问题的追根求源,他说:“思想的追问始终是对第一性的和终极的根据的寻求。为什么?因为某物存有和某物是什么,亦即本质的本质现身,自古以来就被规定根据。就一切本质都具有根据之特性而言,寻求本质就是探究和建立根据。思考如此这般被规定的本质的那种思想,根本上就是一种追问。”伽达默尔则认为问题的提出开启了被问的东西的存在,提问本身就是进行开放。在伽达默尔看来,提问既预设了开放性,同时也预设了某种限制。这种提问的“开放性”和“某种限制”就是“问题意识”或“问题视域”。
“问题”对于教育哲学的优先性关涉教育哲学的本性。教育哲学总须是问题之学,问题对于教育哲学的意义或可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教育问题的追问并非一劳永逸,而教育哲学对教育真理的寻求永远都悬而未决。这正是教育哲学与一切教育科学的本质区别,也是提问所特有的和原始的本质,当然也是教育哲学的本性。因为哲学从其本源意义上来说就是追求智慧而非占有它。伽达默尔在考察问题的发生史时也强调了“问题”一词所表现出的悬而未决的特征。他认为,提问总是显示出处于悬而未决之中的可能性,对于提问不可能有单纯试验性的、可实现的态度,因为提问并不是设立(Setzen),而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可能性的试验。因为很显然,对问题的理解并不能超越我们所处的并由此而进行理解的历史条件。普遍主义的、绝对主义的从而所谓的超立场的立场,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对此,伽达默尔有过精彩论述:“问题是理性本身的产物,理性绝对不能期望有对问题的完满解决。富有意义的是,在19世纪随着哲学问题的直接传统的消失和历史主义的兴起,问题概念获得了普遍的有效性――这是一个标志,表明那种对于哲学的实际问题的直接关系不再存在。所以,哲学意识困惑的典型表现就是当其面对历史主义时,躲进抽象的问题概念里而看不到那种问题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问题。新康德主义的问题史就是历史主义的冒牌货。凭借问答逻辑来进行的对问题概念的批判,必然摧毁那种认为问题的存在犹如天上繁星一样的幻觉。对于诠释学经验的思考使问题重新回到那些自身呈现的问题和从其动机中获取其意义的问题。”当下教育哲学常奢谈永恒的问题,并以拒斥历史主义来占领话语高地,此种所谓教育哲学的超越性不过是一种历史主义的伪装。
其次,教育哲学的追问,并非马马虎虎的追问,而是关涉教育哲学的安身立命。也就是说,教育哲学所追问的问题必须是有意义的问题。问题本身就具有着某种意义,这一意义存在于问题为回答所提供的启示的方向。教育哲学所致力的就在于分析和澄清教育中的核心概念和问题。诸如,人为什么要受教育?谁应该受教育?人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等等。对于这些永恒的教育问题,教育哲学不是一劳永逸地而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和未来做出尽可能认真的回答。每一个时代的教育哲学对这些问题都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给出不同的答案,同时也对当前的回答作出反思。随着追问的不断前行,对这些问题回答的更开放的视域就不断地显现出来,而教育哲学就永远处于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之中――教育哲学不断地进入问题从而获得自身。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哲学研究必须防止高估自己的成果,因为只有问题才是场域和引线。面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意味着面向教育事实本身,而教育哲学愈是植根于对教育事实的分析之中,就越能崭露教育哲学之为教育哲学的本真价值。这种“工作哲学”的思考方式也就是海德格尔所概括的“现象学精神”。他说:“‘现象学’这个名称表达出一条原理;这条原理可以表
述为:‘走向事情本身!’――这句座右铭反对一切飘浮无据的虚伪与偶发之见,反对采纳不过貌似经过证明的概念,反对任何伪问题――虽然它们往往一代复一代地大事铺张其为‘问题’教育哲学不独为现象学,但教育哲学与现象学在对教育本真问题的求溯上,却具有内在一致性。当下教育哲学研究迫切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学态度”。
最后,教育哲学的每一次范式转换归根到底是研究者所思考的教育问题以及教育问题思考方式的转换。从存在形态上看,当下教育哲学有两种研究范式:一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是关注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前者是形而上学的,后者是文化哲学或实践哲学的。形而上学虽然为“教育”提供了可资的思想依据,但是任何对教育“永恒问题”的追问总须是历史与文化的产物。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精神,而教育精神是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教育总得以担当时代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为其行为的前提与指南。当下教育哲学之拒斥形而上学概有两个根本原因:虚假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的虚假。前者是指我们进行所谓的形而上学研究根本达不到形而上学高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教育研究有“本质说”而无“本体论”,这种以形而上学之名行使本质主义之实的所谓形而上学完全败坏了形而上学的荣耀,因为这种本质主义的东西只是纠缠于概念,与价值意义无关;后者是指形而上学的根本弊端仍然在于它把人与世界割裂开来,试图以人的理性去把握这些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无涉的普遍规律,并以此作为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最终根据。我们不能没有形而上学,但形而上学的确有着可疑之处。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你来我往构成了当下哲学乃至教育哲学最基本的纠结。这也许正是当下教育哲学迫切需要直面的问题。
问题以及对问题的思考方式的转换决定了教育哲学范式转换的理性选择。然而,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并不是某种不证而明的东西,走向问题这一说法也仍然有待思虑。
三、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
现代哲学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人的转向、生存论转向、价值转向、文化哲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等为代表的具有“家族相似”意义的一系列哲学转向的提出都内在地揭示了哲学整体性的范式转换。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德里达甚至以宣称哲学终结的方式试图颠覆传统形而上学,既为哲学自身的变革,也为人们对待哲学的态度即哲学观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案。无论这些方案在取向上是如何的迥异,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些学说的内在关联都指向于“问题”。这应该是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发生的时代精神背景。这些方案无疑启示了教育哲学的自我反思,但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并非马马虎虎地依从于这一转向的潮流,而是基于它自身的理论自觉和实践需要。从这一意义上讲,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既具有转向哲学的一般性,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的意蕴。
首先,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意味着某种实践论的取向。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教育哲学是教育理想与终极价值的理论形态,从而执著于理想与价值的逻辑建构。这并非没有意义。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教育理想不是空洞的逻辑言说,教育理想只有回到“粗糙的地面”(维特根斯坦)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理想,这才是教育理想真正的理性。而这就意味着教育哲学必须关注社会实践问题,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以实践论的方式去看待教育。
但实践论并非某种庸俗的实践论,即那种教条式的“实践决定理论,理论对实践起反作用”的实践论,这种所谓的实践论只不过是权利话语的某种巧妙伪装。同时,实践论也并非目前学界所宣称的“理论与实践本然统一”的实践论,这种所谓的本然统一其实是对理论与实践不合的公然逃避。②在我看来,实践论的教育哲学具有如下意涵:一是对教育的任何言说都不能离开人的劳动生产实践,这是教育乃至人类文明产生的前提条件与根源。马克思对此曾明确地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当前教育哲学研究似乎羞于谈及生产物质生活,但这种对“庸俗”的逃避恰恰是对理性的拒绝。因为正是人类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决定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也都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对中国教育的思考,如果离开了中国具体的现实问题,就完全不着边际。二是教育哲学无论多么玄虚,它总不能有悖于常识(common sense)。教育中的“人”以及教育所思考的“人”,是处于现实中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如果教育哲学仅仅停留于概念的、逻辑的思辨,那么教育哲学也就只是头脑中的概念风暴,是想象的而非现实的。教育的真相在常识之中而非在对真理的构造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人和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的。三是教育哲学虽是思辨之学,但思辨并不等于空洞的抽象。教育哲学思辨不是用来满足理念的逻辑要求(比如批判),而必须是直面现实生活的。恩格斯明确提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当教育的种种“原则”大行其道,教育可能正抽身而退。
其次,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意味着教育哲学的文化哲学与社会哲学取向。教育哲学为了能提供对于教育新的洞见,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华丽的说辞或者诸种貌似玄虚实则空洞的奇思妙想,就必须走向具体的生活实践,以文化哲学与社会哲学的视野观照当下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机制。为此教育哲学就必须打破玄思的沾沾自喜而融合到具体科学与文化研究之中。这也是现代哲学发展的大势所趋。文化批判甚至被认为是哲学的本质要求。川罗蒂将现代哲学的这种转型称为新的哲学的范式观,他认为,“哲学”不是这样一种学科的名字:它面对着一些永恒的问题,却不幸不断错误地陈述它们,或依靠笨拙的论证工具批评它们。宁可说它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种“人类谈话中的声音”,它在某一时期专注一个话题而非另一个话题,不是由于论证的需要,而是由于发生于谈话中其它领域的种种事物的结果,或提出了新事物的个别天才人物的创造,甚而或许是若干这类力量合成的结果。很显然,如果教育哲学仍然对当下人的生存状况知之甚少,仍然无力面对中国教育在文化冲突与文化转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那么这种干枯的木乃伊式的哲学也将失去它的活力,从而也将失去它在当下的言说价值。
舍勒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人的生存心态和尺度发生了变化。这实际上是提醒哲学要发掘现代性中人内在的心理状态及其精神动向。有学者曾经提
供了一个转型时期的问题链,如人的内在心理结构、科技与人文、圣俗之间、民族认同与全球化、个性自由与制度法规等。中国教育哲学如何直面这些问题将决定它在一个未知的将来如何定位。如何通过知识整合或者文化整合融化不同文化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何直面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扦格不睦,并从而引导社会确立一种主导性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哲学乃至教育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仅仅逻辑的推理或者心血来潮的哀怨是不够的,它需要教育哲学深入到文化精神的真正寓所中,使内在于生活世界或普通民众中的各种文化因素、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走向觉醒和自觉,这才是教育的真正使命,也是教育哲学的历史担当。做一点踏实的工作,或许教育哲学将由此而获得新生。马克思对意识哲学的批判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而为了走出意识哲学的阴影,教育哲学就必须走向文化与生活。恩格斯的话对当下的教育哲学转型来说仍具有针对性:“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最后,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意味着教育哲学的生活世界取向。回归生活世界对当下教育哲学来说几至成为时髦话语。这是教育哲学的一次伟大进步,同时也是教育哲学又一次虚与委蛇。因为我们的教育哲学仍然停留于原则和教条上,还没有真正在观念上走向生活世界,甚至把走向生活世界本身当成教条。由此当下教育哲学必须形成观照教育生活世界的自觉意识,而不仅仅是其教育哲学式的自圆其说,附带着向愈发陌生的生活世界投去“好奇的一瞥”。
回归生活世界对教育哲学来说不是一种马马虎虎的说说而已,而是一种深刻的范式转换。它意味着:一是教育哲学必须从关心概念、逻辑问题转向关注生活世界的问题。教育哲学的永恒不是表现于它对永恒的理念的解释与再解释,而是表现于它对问题的永恒的关注。马克思曾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教育哲学应该关注的是对问题的抽象而非抽象的问题。这一点关涉如何理解教育的根本价值;二是回归生活世界决定了教育哲学是否虔诚地对待我们的生活。那些“虔诚”地对待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能够以追根溯源的理论姿态,叩问教育的内在性和本性,因而能够紧紧抓住人的心灵,在文明危机中追求人的尊严和崇高。胡塞尔曾把近代哲学史看成是为人的意义而斗争的历史,他甚至认为,“我们时代的真正唯一有意义的斗争是存在于那些已经崩溃的人与那些还保持着根基、并为了这一根基以及新的根基而拼搏的人之间的斗争”。既然教育哲学承认教育的使命在于追求人类福祉,促进人类幸福,那么抽象的幸福也只有放置在生活世界里才有可能获至它的根基。三是教育哲学必须清算知识论哲学和机械论哲学的谬误与虚假,这本身也是现代教育自我救赎的一次有益探索。因为回归生活世界的教育首先坦露了教育从生活世界中的“脱离”,而教育之脱离生活世界则主要倚助于知识论哲学和机械论哲学才有可能。如果我们的教育哲学尚未进行这样的工作,那么所谓的向生活世界回归也就只能是句空话。
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不是对教育哲学的“消解”,毋宁说是“再生”。它是教育哲学重新获得其荣耀的涅�,也是教育哲学真正沉思的担当。在一个以批判马克思主义为时髦的日益喧嚣和浮躁的时代里,我们需要重温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作为从事教育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忠告: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因为教育哲学研究者面对的不仅是“教育哲学”这一学科,也承担着中国教育哲学的新生和中国教育的改造。中国教育哲学的根在中国教育,我们永远不能忘却这一点。再没有比面对当下如此巨大的“中国文本”置若罔闻更令人失望的教育哲学了。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哲学也就是在思想中把握的它自己的时代。对当下的中国教育哲学来说,此处吃紧,不得不察。
[参考文献]
[1]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M].孙周兴,选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衣俊卿.回归文化批判:哲学的本质要求[J].社会科学战线,2003(3).
[8]欧阳康.哲学问题的实质与当前哲学研究的问题链[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9]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下一篇:没有了
更多网站公告
- ·国家级杂志《社会科学》刊期说明 2016-07-20
- · 国家电网主管主办的电力专业期 2016-06-23
- · 办公类核心期刊《办公室业务》刊 2016-04-28
- ·《临床肺科杂志》统计源核心期刊 2016-01-22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 2015-01-09
- ·中国教师论文发表网为您出书 2013-02-26
- ·教师发表论文请找中国教师论文发 2010-01-12
- ·中国教师论文发表网郑重承诺 2008-12-28
热门阅读
- ·当代教育哲学的“问题哲学”转向 [06月02日]
- ·宗教哲学的角度浅谈宗教与哲学的 [06月02日]
- ·现象学哲学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 [06月02日]
- ·后现代哲学思潮与科学哲学的重建 [06月02日]
- ·黑格尔哲学中哲学美的存在 [06月02日]
- ·新时期的哲学之“用”与应用哲学 [06月02日]
- ·哲学知识与哲学智慧 [06月02日]
- ·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 [06月02日]
- ·哲学思维方式与哲学变革 [06月02日]
- ·从企业实践看领导干部学哲学、用 [06月02日]

电话:15554080077 邮箱:chinajiaoshi@163.com QQ:546427774 102763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