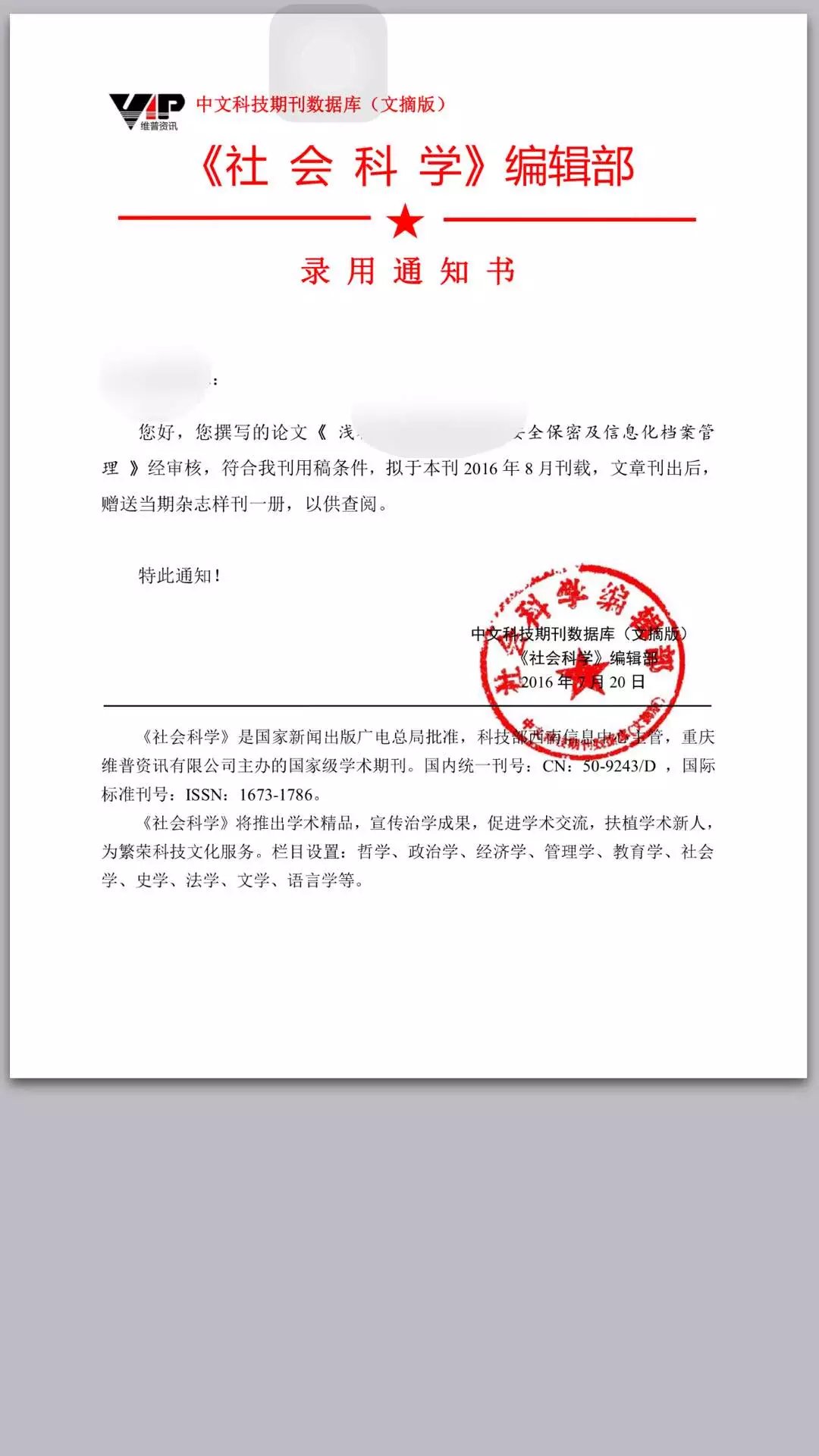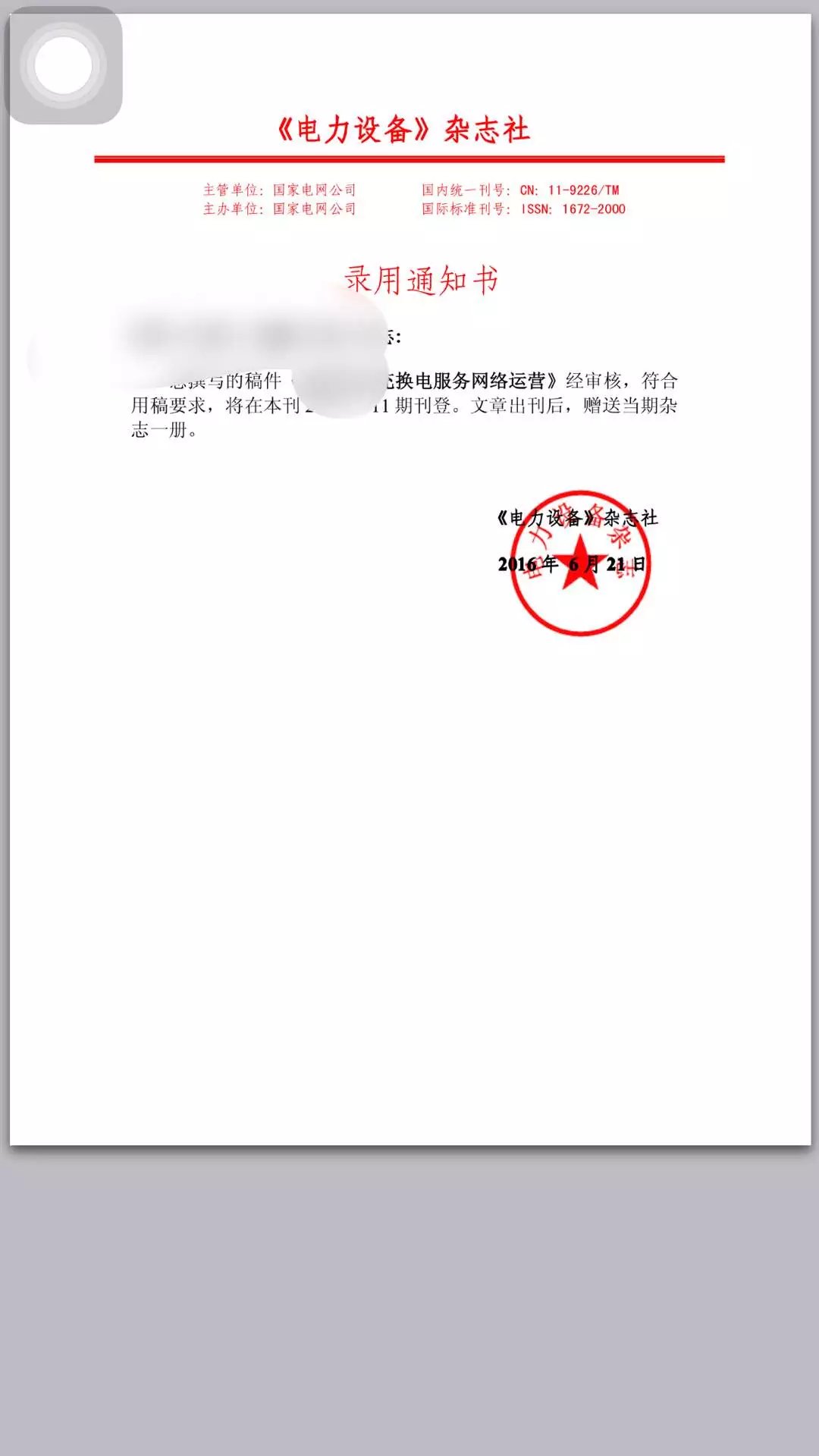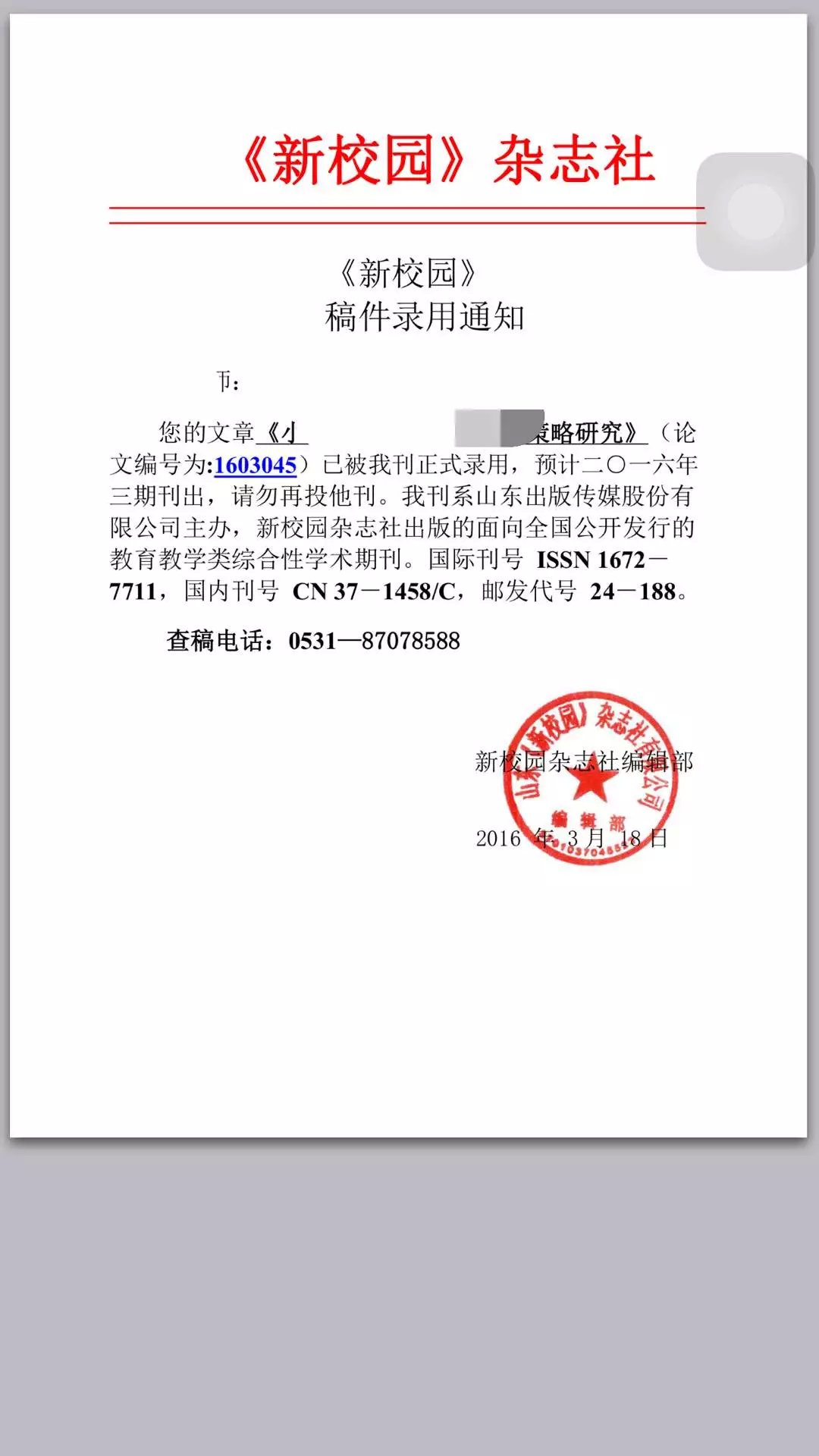谈文学作品阅读中“形式”的领会和把握
在最新使用的高中教材中,出现了大量的西方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它们都是艺术性很高的作品。所谓的“艺术性”,其实与作品的“形式”有很大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形式”,决不像人们日常所比喻的那样,仅仅是一件漂亮的外衣,它不仅指外部的东西,也指作品内部的某些东西。按照当代文学艺术观念,“内容”似乎位于艺术的范围之外。一部作品的艺术生命的长短,一部作品艺术性的高低,常常取决于它的“形式”。当然,我们认为:“形式”是在与内容的配合下达到它久远的艺术生命力的。
这就可以看出,对“形式”的把握和领会是如何的重要。对这些优秀之作,并不适合做一味的中式解读,它们从观念到制作,都有一定的理论。拙作《试谈文学作品阅读中“意义”的领会和把握》(见2000年第4期《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曾经隐约地谈到过作品的“形式”问题。
一个艺术家受其天资、劳动、创作个性,受其文化的、个人精神的以及思想审美方面的影响,使他拥有了独特的创作方式和创作技巧。文学创作技巧,在这里,就是我们说的“形式”。它一般表现在独创性、手法、选题、构思、情节和布局安排等上面。当然,属于一部作品形式方面的东西还有独创性、情节、风格、叙事人问题等等。完整的形式具有一系列的特征,诸如和谐性、表现性、独创性等等,它们在一件艺术品中形成一个统一体。
文学家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总在创造“新的形式”,他不愿步别人的后尘,和别人一样,简直就是自杀。所以一部优秀的作品总是独特的,总有它的时代的领先性。贺拉斯说过,平庸的作品是人神共嫉的,连书贾也不容。沃尔夫《墙上的斑点》是一篇意识流小说,一个敏感的纤细入微的女性,用她的心灵在感受一个微小的事物,很快就变成了别具一格的作品。有时候,创造,就是跟心索取,跟精神索取。外部世界里并没有摹本,别人那里也没有摹本。人本身就是一种脑子里面始终在“发生”着想法的动物。世界并没有意义。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不是人能用人间的“意义”所概括得了的。人脑瞬间、随机、连续可又不合逻辑地“发生”着各种念头,这应该就是人的本质之一。沃尔夫《墙上的斑点》这种小说文本其实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人”做了一张标本,可以出示给外星人看,可以告诉我们人就是这样,以便于我们人了解自己、进而了解世界。意识流小说就是以人的意识为描摹蓝本,它的意义就是反映出世界的没有意义。一种敏锐、细腻、丰富、甚至是病态的感觉,对文学来说,是重要的,一种对意识忠实得像义犬一样、又极尽舒缓、与意识的形状对应吻合的华美语言对这一类非叙事文学来说,也是重要的。意识流是一种可以“从内部”描写人的心理过程的手法,可以更加无拘谨地展示主人公的真正的精神状态。独白,也是一种意识流,哈姆莱特、自杀前的安娜·卡列宁娜、屈原(《雷电颂》)都把内心丰富复杂的感情做了尽情的流露。在现当代西方作品中,意识流手法已经广为使用。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乔依斯的《尤里西斯》的现代作品大大复杂化了意识流手法,采用意识流手法,并把它作为艺术手法之一放在整个作品中,使得主客观和谐地结合起来,是托马斯·曼、海明威、罗曼·罗兰他们获得现代性认证许可的一个因素。
关于创作的独创性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独创性表现为内容的新颖和使用新的大胆的手法刻画旧事物。文学史上有许多流派,都有着鲜明的独创性,但是过分的追求就会变得离奇,变成标新立异。黑格尔说,风格的真正独创性在于看不出独创性,也就是藏而不露,作者和作品本身融为一体。很多经得住反复推敲的大作品都是这样,比如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他的艺术风格简洁明朗得就好像是海上的风和明亮的光一样。
在作品中使用怪诞的手法,能造成离奇和滑稽的效果,把互相排斥的东西进行魔幻般的组合,利用各种对比和怪异、畸形的表现,来震惊人们的想像力,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属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作。一个艺术家在全国巡展,表演自己的绝食,这本身就隐含了对人世的一切的拒绝态度,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对世界深刻的洞悉,他并不想说出来(语言是苍白的),他要用自己的独特的形式“做”出一个结论来。最后,他把他自己做成了一个别致的样本,给世人看。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标本。标本里面,饱含着人的本质(人的精神追求的终极时段的危险性)和世界的本质的丰富内涵,还有人的生存处境的险恶等等。据说,卡夫卡去世前一个多月在病榻上校阅这篇小说时,不禁泪流满面。贝克特《等待戈多》,等待的是一个始终没有到来的人物。这就是在西方艺术家眼里的世界的意义。也许,作品所暗示的远远比“人的一生的徒劳”这一个意义更多、更深远。当艺术品否定了一个单一的主题认识以后,它就获得了暗示更多的意义的资格,也就找到了它本身与复杂世界的真正的“多义”的对应。至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写法上,蓄意对现实主义手法进行破坏,把文学的古老的魔幻的神奇特质重新磨亮了。此外,现代小说家极其推崇的大师妥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豆子》中的死人说话,果戈理《可怕的复仇》中死人从地下长了出来,还有斯威夫特、布莱希特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在借这些荒诞的手法来真实而强烈地表现现实世界的矛盾,表现人对世界的荒谬感受。
有时,荒诞派的作品给人莫名其妙的感觉,但细加思索,就会觉得其深刻。他们的创作与他们所持的观念有关。荒诞的定义来自加缪,加缪在《西西弗斯之谜》中说:人决心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目的和秩序,而世界却坚决拒绝证明有这两样东西,由此而产生的紧张就是荒诞。荒诞派戏剧摒弃了情节线索、人物性格的发展和理智的语言。贝克特《等待戈多》、尤内斯库《秃头歌女》是写于40年代末的经典。荒诞派剧作家认为,人类显然生活在一个不合理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无法交流思想,幻觉代替了现实。个人没有真正的行动的范围;人越来越多地受到了物质世界的挤压,成了牺牲品;人的品质,例如坚韧和勇气的惟一作用只是对人的无能为力进行嘲笑,此外没有别的任何作用;个人的原动力,即基本的本能和反应成了他苦难的根源。加缪认为:荒谬、反抗等运动的目标就是怜悯,即归根结底就是爱。加缪还认为荒诞派作品的风格就是直接表现主题。
西方当代文艺理论认为,“情节”的定义就是艺术地思考和组织事件的方式,即,把本来的生活材料进行艺术变形。要想真正地领会作品中的情节,要把它和现实生活事件做比较,或者通过纪实性的作品来做对比,方能清楚地显现出来。情节被看着是一种加工,即赋予素材以形式。情节也是作家艺术地领悟世界的一种方式。最常见的一些变形的方式是:打破时间的系列的不可动摇性,重新排列事件和行动的发展。比较复杂的是利用场景之间的非直线联系,也就是把情境、人物和场景勾回连环地艺术地呼应起来。
比如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是典型的情节上的佳构,整部长篇小说把海明威自己在西班牙战争中的经历浓缩在主人公执行爆破任务的几天里。课文节选部分着力在战争中表现人性。小说结尾的情节是这样的:罗伯特·乔丹已经受伤,无法撤离,敌人就要到来,战场只剩他一个人,他注定就要死去,而小说的情节进展戛然停止。在这里,情节,体现了它情节之外的深度。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对生死的体悟,在战争这个特定的场里,被几千倍地放大了。他已经濒于死亡,他成功地让自己的女朋友走了,他一个人和孤独的战场为伴,开始思考自己从哪里来,家里有些什么人,想一切东西,想一切的人在临死之前都要想的事。最后,他准备在追击的敌人进入他的有效射程之内时,用他精疲力竭的手臂端起枪,抠动扳机。海明威故意让小说就这样“遗憾”地结束,他故意不把情节写完整,敌人并没有到来,罗伯特·乔丹也没有下文,而最后一页已经读完。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也把情节变得非常紧凑集中。在一艘象征人世漂浮短暂依存的轮船上,各种人相遇了。一个隐蔽身份的人战胜了世界冠军,但他的危险而可怕的生命经历被唤醒了,他在棋盘中复发了旧病。在任何一个人生的“眼前”的遭遇中,都能拖出一条“过去”的人生历程的长蛇。人就是这一种动物,人为什么会痛苦,为什么会老去,为什么会死亡,都是因为这个。这个故事向我们讲的远远超过了这些。在现代派艺术中可以看到一种追求无情节性的倾向,沃尔夫《墙上的斑点》就是没有情节的作品。但是,一般而言,即使在今天,在西方艺术家眼里,情节也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根据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家给的定义,风格是作者给他的作品打上独特印记的方式,是不能进行逻辑分析的一种东西。风格能表示艺术家比较深刻的本质特征。这在赵树理和孙犁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现代作品中,西方文论特别重视对于“叙事人”的理解。传统的那一种中立、客观而又无所不知的“无人称”的叙事方式,逐渐被抛弃。这里有一个反面例子:如果传统作家莫泊桑在他的《项链》里安排一个别的叙事人,那么他的观点的短拙之处(世界观的马脚)就会得成功的遮掩。如今,很多优秀作品都有一个被作者控制的“人物”在代替作者讲述故事。这一个确定的人,其实是作者自己的艺术形象,是作者虚设的一个自我,是代自己行事的,(例如鲁迅作品中间的“我”,总让人分不清是不是作者。)作者对所发生的事件的理解和评价,照样不露痕迹地表现了出来,但通过设置好了的一个新的代言人,这种表达就变得曲折(非直接)得多了,变得可信度高多了。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这一点上做得更为大胆和出色,他在《喧哗和骚动》中大胆地采用了多个叙事人的做法。
作者和叙事人之间有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既可以相同也可以相异。在《变形记》中,格里高里变成了一只乌龟,“我”作为人的资格的丧失和非人的身份的获得,这一些深刻的意味的出现,与这个“叙事人”角度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关系。
冲突,也属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素,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戏剧性作品中)很多地被设置。人与自然的搏斗(《老人与海》)、不同性格之间的对抗(《雷雨》)、主人公和社会环境的撞击(《信陵君窃符救赵》)、身份和地位的矛盾冲突(《廉颇蔺相如列传》)、痛苦的内心体验活动(比如很多抒发性灵的现代诗歌)等,中间都有鲜明的冲突。冲突被理解为是人物的性格、思想、欲望和利益的对抗,冲突的戏剧性强度是作家非常讲究的。它可以到达情感激动的高峰,造成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这一种冲突的解决,正好说明了矛盾的根本不可能解决(《雷雨》、《茶馆》中的很多对矛盾都是这样)。埃及小说家、戏剧家台木尔《纳德日雅》写了人的本性(与生俱来的亲情)受到了后天的“荣誉”的戕害,表现了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为了名声,为了纯洁,为了面子,为了一个号召,人们被情绪支配着,丧失了理智,也背离了本性。人并不能支配自己,人越有知识,人就越愿意为虚假的东西而奋斗。就是在这种人与人自身的内在的冲突的意义上,这一部作品获得了成功。
艺术象征作为一种表现手段,纯粹是由作家自己创造出来的,就跟隐喻和比喻的创造一样。艺术象征这一种表现手段和别的手段不一样,别的艺术手段一般来说只拥有一个基本意义,而象征则能营造晕轮效应。艺术象征是多义的,艺术象征是反对赤裸裸描写的一种结果。
暗示,是词语的弦外之音或者言外之意,作家使用这样的词,借助于人们的联想,往往可以达到非常高妙的艺术效果。无疑,鲁迅是这一方面的大师。影射,即含沙射影,不是在句段里,而是在整个篇章范围内广泛使用的艺术手法。像T.S.艾略特的《荒原》,作品中充满着丰富的形象、象征和反讽,理解这一些作品,暗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无法绕开它。
在普鲁斯特、乔依斯之后,进入了现代小说的时代。根据英国文学辞典,现代小说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将外部世界(客观事物和事件)降格,除非它们有象征意义;第二,小说家全神贯注于时间;第三,对叙述技巧和叙述程序进行反复的实验。现代小说继续对意识予以注重。关于同时发生的事情和先后发生的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时间展示出两个相度,两个流和两个束,一个里面流淌着另一个,使得时间之流浑浊起来,复杂起来,人们想彻底抛弃“叙事人”,在作品中,不评价不议论,达到零度叙述的程度。
更多网站公告
- ·国家级杂志《社会科学》刊期说明 2016-07-20
- · 国家电网主管主办的电力专业期 2016-06-23
- · 办公类核心期刊《办公室业务》刊 2016-04-28
- ·《临床肺科杂志》统计源核心期刊 2016-01-22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 2015-01-09
- ·中国教师论文发表网为您出书 2013-02-26
- ·教师发表论文请找中国教师论文发 2010-01-12
- ·中国教师论文发表网郑重承诺 2008-12-28
热门阅读
- ·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学习习惯的塑 [01月16日]
- ·高中语文教学中求异思维的应用 [01月16日]
- ·高中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作 [01月16日]
- ·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学习能力的培 [01月16日]
-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文言文教学 [01月16日]
- ·高中语文教学中别让学生成为被动 [01月16日]
- ·传统文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融入 [01月16日]
- ·高中语文教学中人格教育渗透 [01月16日]
- ·高中语文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的开 [01月16日]
- ·如何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01月16日]

电话:15554080077 邮箱:chinajiaoshi@163.com QQ:546427774 102763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