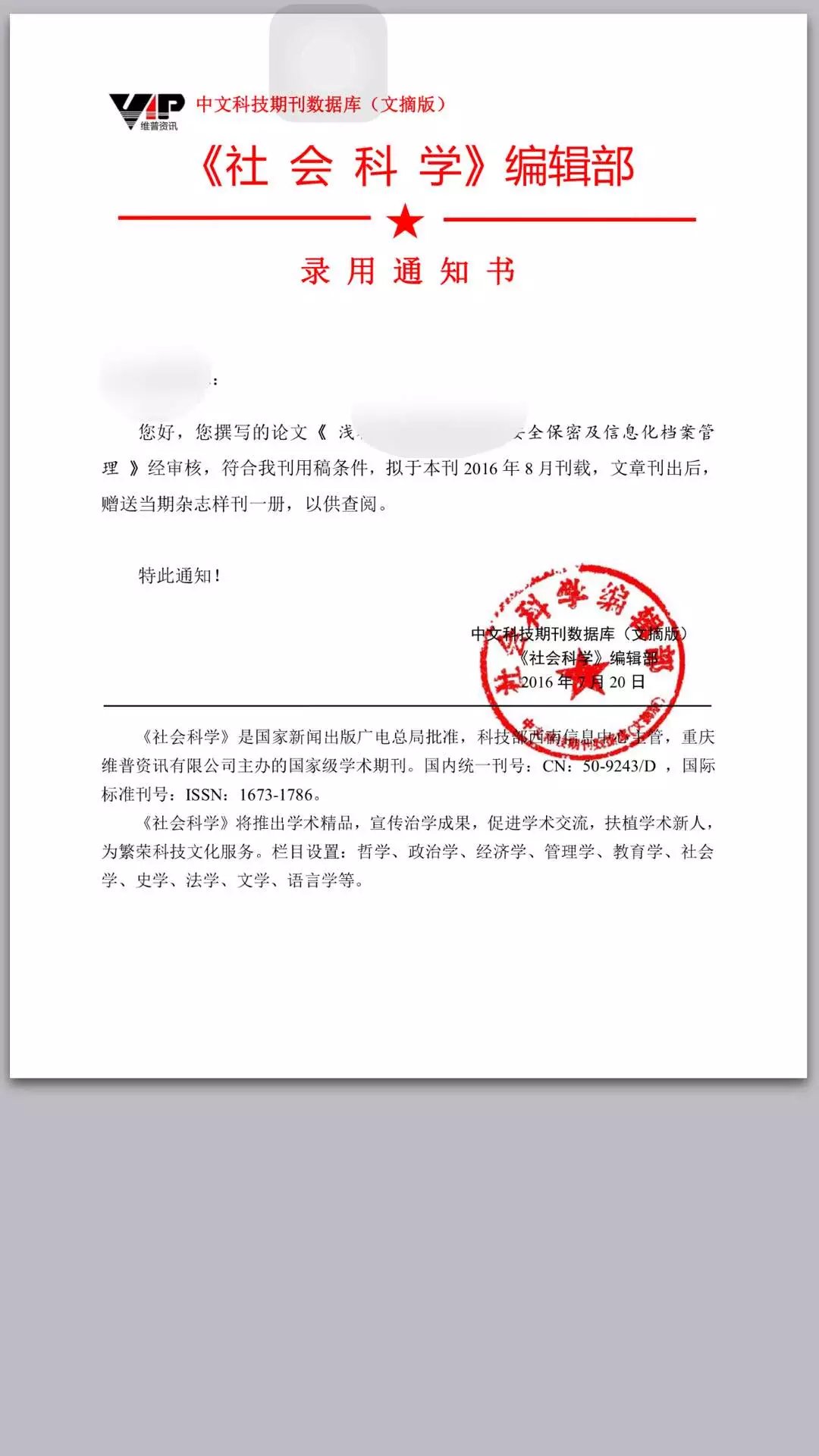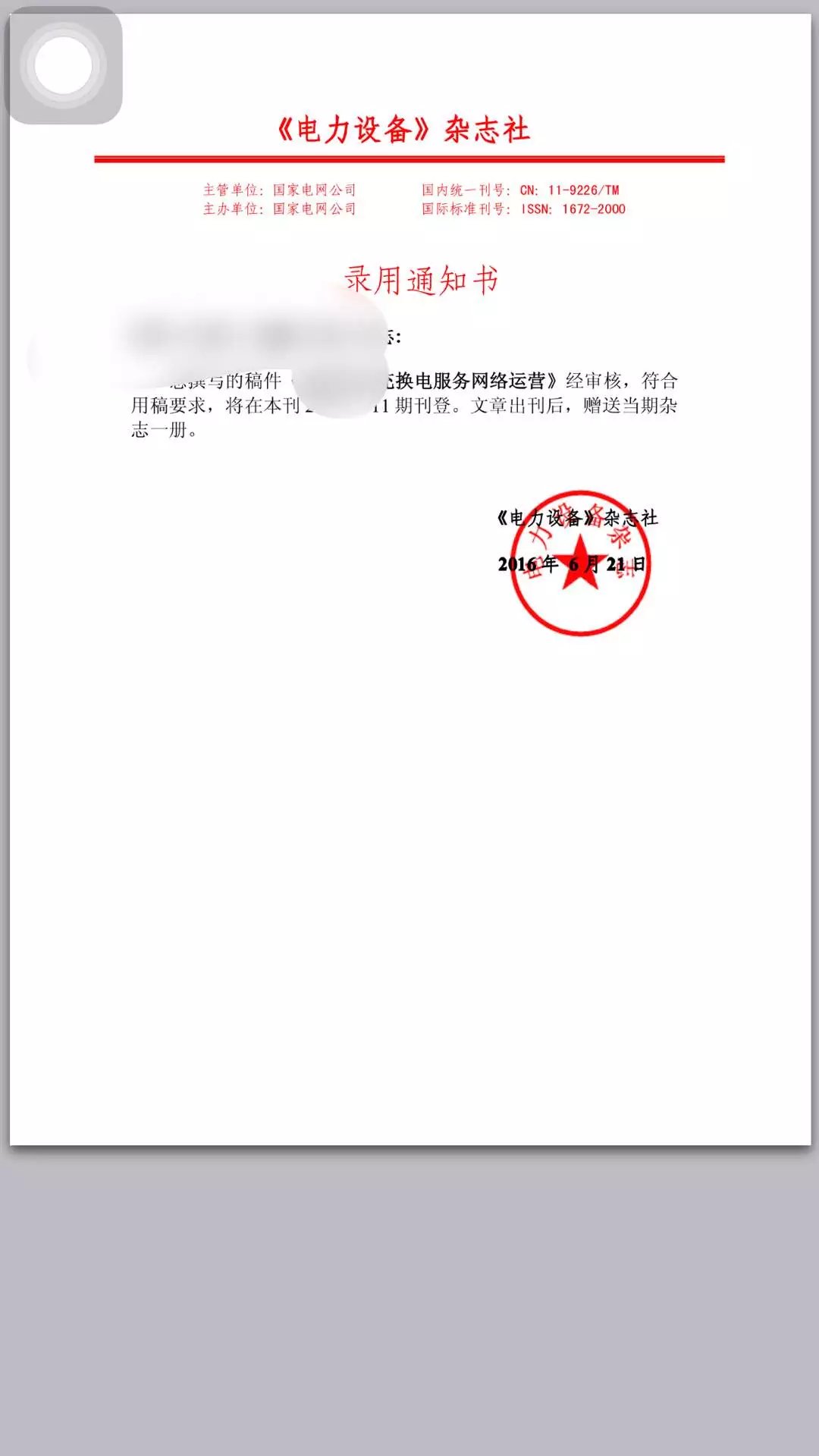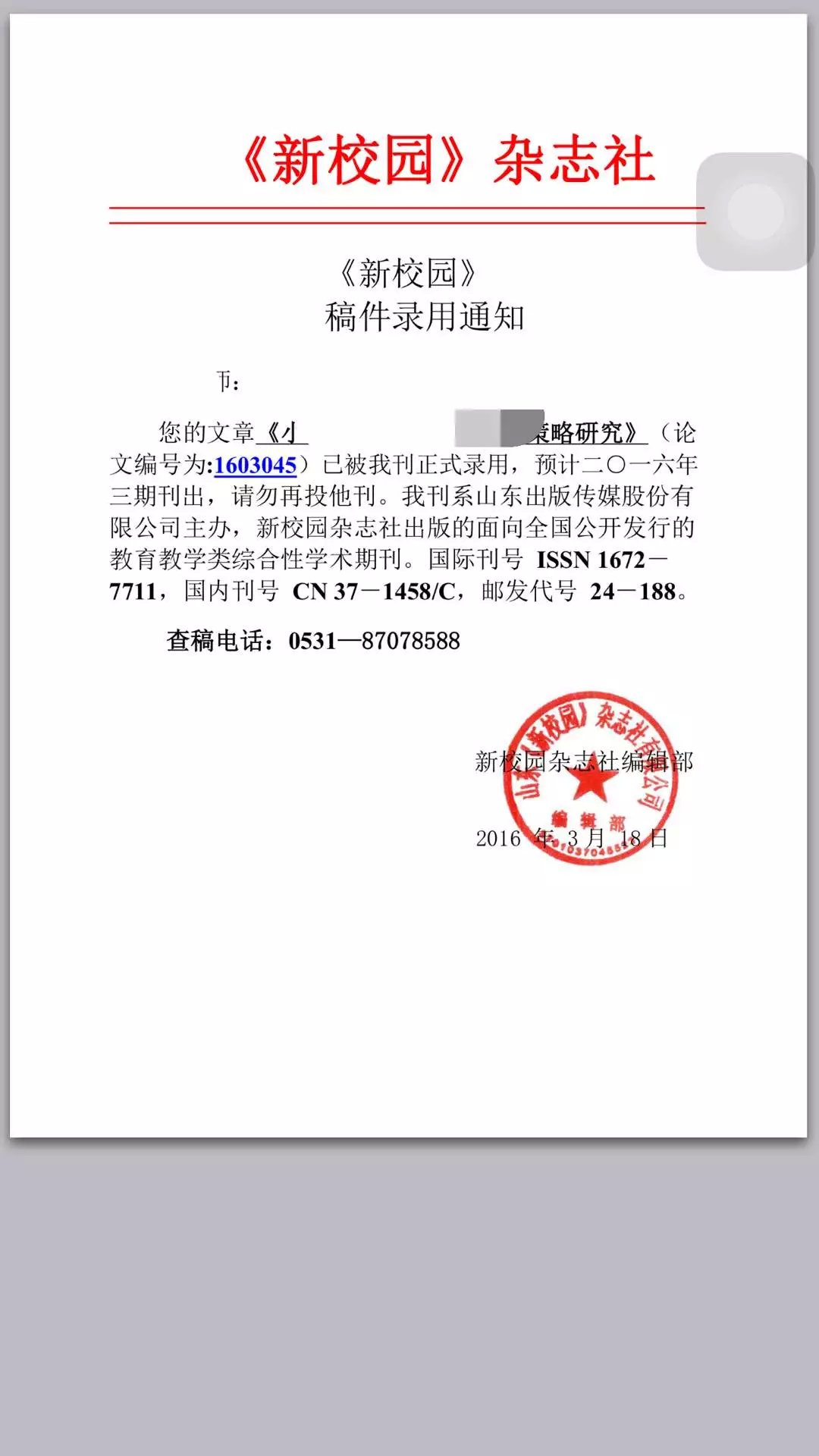贵州城镇化发展中民族文化适应研究
摘要:贵州省“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已启动四年,即将完成“五年规划”,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进一步探究在贵州这样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开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民族文化适应问题是有检验意义的。从当前情况看,工业化和城镇化冲击着民族和民族文化生态,而民族文化做出必然反馈,以一种观望和逢迎、被动与主动并存的姿态做出“神经性反应”,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而其矛盾现象的释解有赖于时间性概念的介入和生活秩序的重建。
关键词:工业强省 城镇化带动 民族文化 文化适应
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要重点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贵州省原省委书记栗战书强调贵州省发展的是生态主导型工业,只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走持续发展的路子就能成功。这是兼顾生态环境而做出的贵州快速发展的顶层设计,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上看,是有其科学性的。工业发展从生产力提升上给贵州发展提速,但也必然引起贵州多民族社会生态的变迁,其中民族文化适应的话题就无可避免地构成了探讨的可能性。目前,针对贵州这一特定场域、特定事件下的特定行为的研究还没有相关研究成果,但这一研究视域的重要性是可预见的,也有实践价值。
1.生态变迁与逻辑变更:“场域”视角下的分析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内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在各种客观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它是独特的,它不是对社会单纯的空间分割,也不是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而是指有一定文化特征因素在其中作用的相对独立的具有社会性的场域[2]。在这个场域内,其运行规律和方式等均遵循其特定的逻辑,有其必然性,而且这种特定逻辑和必然性在“他者”场域内并不通行。
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其构成的也是一个特定的“场”,其自身逻辑为特定的行动表现做出归因。当工业化打破原有农业生态,并城镇化改变着其生活逻辑,一种变迁的姿态自然出现。于是,不同场域因素在作用与反馈间用博弈的姿态进行磨合,构成一个调适的弹性空间。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成分十分多元的省份,民族地区农村比例较高,在城镇化过程中,一种崭新的顶层设计开始介入到这些农村社区,并用迁移合并或就地改造的过程完成一个城镇化过程,将原有的场域性打破,构建一个新的场域,其中作为一定场域性惯习的承载者,就无可回避地面临适应与否的调适。
每个民族或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系统,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都会做出一些反应,以求对外来文化达到适应状态。贵州民族地区多为一个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他们形成了一种基于地域共性和民族共性的文化场域,面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其文化调适行为必然发生,首先体现在文化持有者身上。
2.被动观望与主动逢迎:基于现实的矛盾表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围绕社会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纽带,相互往来,各种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结合体。相对外部而言,这种结构体系较稳定,而其内部的多元因素实际上不断互动着,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互动。随着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介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将发生变迁,各种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文化生态的种种变迁,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形式的当地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馈,而这种反馈具有主动适应的一面,也有被动不适的一面。
从对贵州毕节试验区的调研情况看,面对城镇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被动行为做出“神经性反应”,跟随城镇化步伐而律动。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并未构成一种可能基于自觉行为的结果。毕节七星关区的建设牵涉到诸多城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以苗族、彝族农村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些,不同民族之间对于城镇化过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应具有一定的类同性,不少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动观望,有的则是主动逢迎,而这种矛盾的归结点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动,尤其是经济利益信息对于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虑也无法尽释。比如祖业的固守观念、宅居风水的留恋,以及展现在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和行为的困惑等。这种不适应的受访对象中,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展现出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适应度基本遵循“从老到小”的递增规律,即老人对于变更传统的行为相对较为保守一些,表现出来的不适应程度深一些,而新时代更为适应这种变迁。
工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外部的文化力量就会不断介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不断进入的因子和作用,当地的文化就会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对之做出反馈。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将出现新的现象。一般来说,以经济力开道的城镇化往往带给当地人的是愉悦与困惑同在。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各种新鲜事物,满足了审美新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也确实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进步,因而愉悦;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因子不断接触传统或民族性或区域性的文化形构时,就会使他们感受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短期困惑:是该抛弃传统,还是固守传统?当各种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兴起之时,引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当地民众处于一种观望和迷茫的状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文化事像,他们所做出的文化反馈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
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种外来文化,最初给当地民众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新奇感,带来暂时性的愉悦和欣喜,而当新鲜热度消退之后,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潜层的矛盾与困惑,有一种传统割离感。当然,这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关的,不同的民族群体反馈出来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传统变更与断层却难免出现阵痛。
3.生活秩序的重构:时间性概念下的持守与超越
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力量的迅速加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各少数民族所喜见的,而有的变化却给他们带去暂时的不适甚至是困惑。种种不适与困惑,多为文化上的反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各民族如何实现文化适应,值得我们认真关注。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都会面临新的适应的问题。只要外来文化对被介入的文化体系没有构成解构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间都会出现双向的适应。文化适应的日常表现往往是一种自在的行为,是一种相互运动最后达成协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关键。
民族地区的文化形式多样,适应的内容就会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区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动体系,尽管经过了历史的磨合,各多元主体之间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谐的结构体,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看,其民族群体关系也就具有了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是一种调适的状态。在这种内部调适持续的情况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变了原本的状态,打乱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在外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内部结构暂时的失衡,但原有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主体性的文化根基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挑战、冲击、剌激,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会或被动或能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称为文化调适。文化的适应是在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对于异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抗拒,对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废弃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个民族和某一区域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多少都会有保持各自文化边界的心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们之间在作用与反馈过程中,先是无序的反馈,再到有序的适应过程,只是时间性元素的多寡影响不一。
具体讲,在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与反馈总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的纠缠状态,不断地将无序的作用与反馈导入到有序的系统中来。通常,某一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做出线性反应,而是透过文化自身的调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其内部结构都是有序的,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发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馈却不一定是有序的,因为其中既有个人随机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适应初期无序的作用与反馈,以及由此还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尽管连续呈现无序状态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适应最终总要达成。文化适应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再无界限,而是多种力量关系作用下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3]中表达的生活的常态:徘徊在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在林老看来,变化不一定导致框架坍塌和社会无序,平衡是生活中的变态,而不断地寻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文化适应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适应是必然的,文化不适应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表现。
从现实过程表现看,文化调适主要围绕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变迁这两条线索展开,其结果是对发展着的现状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总是在文化互动中得到结果。经过互动,相互进行接触、碰撞和磨合,达成一种有序的适应状态。当然,在这种互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或者促成原有体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过程,其实质也是适应的过程。文化互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时不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是不同文化符号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张力博弈的过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适应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构为依托的。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几种文化互动作用之后,会出现一个“次生文化”的问题,即面对文化的变迁,文化互动 的双方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形式来协调互动不适的问题。文化适应的过程,尽管存在作用力悬殊,但其过程是双向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改变传统社区格局的同时,民族地区元素也在对这种新兴的城镇产生影响,并在某种范围内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对这种具有政府力量主导的城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过程多半处于被适应的地位,只是这种被动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坚守。所以,这是一种时间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与超越。
事实上,民族文化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面对变迁,其适应与否的话题皆与其生活秩序息息相关。工业化、城镇化必然打乱民族社区原有生活的格局与常态,不适的反应必然出现,但只要时间性概念的介入,并进一步把新的生活秩序建构起来,那么基于新的场域性构建,一种适应的逻辑和必须性就无可避免地形成并发挥作用。所以,“工业强省”背景下的城镇化发展,如果坚持生态主导型发展模式,兼顾文化多样性生态保护,那么民族文化适应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瞿琨.场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发展[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32.
[3]林耀华.金翼[M].三联书店,2007.
更多网站公告
- ·国家级杂志《社会科学》刊期说明 2016-07-20
- · 国家电网主管主办的电力专业期 2016-06-23
- · 办公类核心期刊《办公室业务》刊 2016-04-28
- ·《临床肺科杂志》统计源核心期刊 2016-01-22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 2015-01-09
- ·中国教师论文发表网为您出书 2013-02-26
- ·教师发表论文请找中国教师论文发 2010-01-12
- ·中国教师论文发表网郑重承诺 2008-12-28
热门阅读
- ·网络营销策略的分析与研究 [04月30日]
- ·浙江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公民海 [04月30日]
- ·国际营销策略研究 [04月30日]
- ·内地不动产登记制度与澳门不动产 [04月30日]
- ·医院档案管理应用信息化手段探究 [04月30日]
- ·工会在稳定队伍中发挥的作用 [04月30日]
- ·和谐医院构建过程中工会组织的作 [04月30日]
- ·适应国内马术运动迅猛发展的管理 [04月30日]
- ·通州地方海事精神的表述与作用 [04月30日]
- ·韩国软件人才培养政策分析 [04月30日]

电话:15554080077 邮箱:chinajiaoshi@163.com QQ:546427774 1027630087